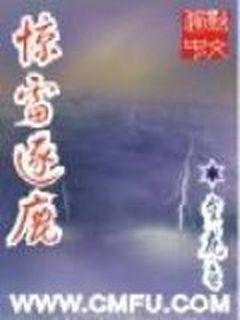- [ 免費 ] 第壹章 屠戮
- [ 免費 ] 第二章 雷門
- [ 免費 ] 第三章 三少
- [ 免費 ] 第四章 長安
- [ 免費 ] 第五章 胡姬
- [ 免費 ] 第六章 提督
- [ 免費 ] 第壹章 下車伊始
- [ 免費 ] 第二章 伯顏察兒
- [ 免費 ] 第三章 馬如龍
- [ 免費 ] 第四章 祁連山
- [ 免費 ] 第五章 青海灣
- [ 免費 ] 第六章 指點江山
- [ 免費 ] 第壹章 雛形
- [ 免費 ] 第二章 文韜
- [ 免費 ] 第三章 斬首擒王
- [ 免費 ] 第四章 完美殺戮
- [ 免費 ] 第五章 秘會
- [ 免費 ] 第六章 變數
- [ 免費 ] 第壹章 妥協
- [ 免費 ] 第二章 溫室與冰窖
- [ 免費 ] 第三章 歸途遇襲
- [ 免費 ] 第四章 戰爭販子
- [ 免費 ] 第五章 群英初會
- [ 免費 ] 第六章 勢所必然
- [ 免費 ] 第壹章 沮喪
- [ 免費 ] 第二章 馬賊與天災
- [ 免費 ] 第三章 隴右總督
- [ 免費 ] 第四章 雷厲風行
- [ 免費 ] 第五章 夜未央朱粉樓
- [ 免費 ] 第六章 錢途
- [ 免費 ] 第壹章 我是馬賊
- [ 免費 ] 第二章 弓刀血火雷噬
- [ 免費 ] 第三章 回響余音
- [ 免費 ] 第四章 雪後賑災
- [ 免費 ] 第五章 立地成佛
- [ 免費 ] 第六章 歸途踏雪
- [ 免費 ] 第壹章 上元狂歡,禁令橫來 ...
- [ 免費 ] 第二章 困局何解?
- [ 免費 ] 第三章 赴戎機
- [ 免費 ] 第四章 縱橫塞外戰血流 ...
- [ 免費 ] 第五章 戰士長歌入漢關 ...
- [ 免費 ] 第六章 試拂鐵衣血斑斑 ...
- [ 免費 ] 第壹章 世事如棋人作子 ...
- [ 免費 ] 第二章 白銀騎士鏖戰急 ...
- [ 免費 ] 第三章 魅仙妖蝶舞蹁躚 ...
- [ 免費 ] 第四章 南歸
- [ 免費 ] 第五章 走私
- [ 免費 ] 第六章 歸去來
- [ 免費 ] 第壹章 血染天馬園
- [ 免費 ] 第二章 東風破堅冰
- [ 免費 ] 第三章 誘惑危機
- [ 免費 ] 第四章 伏兵羅網
- [ 免費 ] 第五章 血腥劫奪
- [ 免費 ] 第六章 寶馬識途美人嬌 ...
- [ 免費 ] 第壹章 醍醐灌頂
- [ 免費 ] 第二章 騙人有術
- [ 免費 ] 第三章 秘室議事
- [ 免費 ] 第四章 囹圄
- [ 免費 ] 第五章 生辰·黃綾
- [ 免費 ] 第六章 驛館幽情
- [ 免費 ] 第壹章 諜影京華
- [ 免費 ] 第二章 只身入京
- [ 免費 ] 第三章 覲見皇帝
- [ 免費 ] 第四章 皇庶子
- [ 免費 ] 第五章 畸門?奇門?
- [ 免費 ] 第六章 “酒”能亂性
- [ 免費 ] 第壹章田獵·火器
- [ 免費 ] 第二章 猛虎薔薇
- [ 免費 ] 第三章 烈火燎原
- [ 免費 ] 第四章 大疫·掘金
- [ 免費 ] 第五章 都督軍事
- [ 免費 ] 第六章 鴻鵠西飛
- [ 免費 ] 第壹章 酒徒高陽
- [ 免費 ] 第二章 四顧躑躅
- [ 免費 ] 第三章 霍州敗績
- [ 免費 ] 第四章 以迂為直
- [ 免費 ] 第五章 烽煙四起
- [ 免費 ] 第六章 最高危機
- [ 免費 ] 第壹章 爭奪隴山
- [ 免費 ] 第二章 都督幕府
- [ 免費 ] 第三章 文化人心
- [ 免費 ] 第四章 立國之本
- [ 免費 ] 第五章 閨中人語
- [ 免費 ] 第六章 論戰陰謀
- [ 免費 ] 第壹章 不速之來客
- [ 免費 ] 第二章 秘晤之僵局
- [ 免費 ] 第三章 血腥之清洗
- [ 免費 ] 第四章 先發欲制人
- [ 免費 ] 第五章 勝敗難定論(上) ...
- [ 免費 ] 第六章 勝敗難定論(下) ...
- [ 免費 ] 第壹章 輕煙樓上
- [ 免費 ] 第二章 “大元帥”
- [ 免費 ] 第三章 僑民血淚
- [ 免費 ] 第四章 流民天下
- [ 免費 ] 第五章 紅顏天驕
- [ 免費 ] 第六章 刑殺立威
- [ 免費 ] 第壹章 磨礪刀鋒
- [ 免費 ] 第二章 先利其器
- [ 免費 ] 第三章 步兵軍團
- [ 免費 ] 第四章 結盟之途
- [ 免費 ] 第五章 橫行青海須帶刀 ...
- [ 免費 ] 第六章 暗流無聲
- [ 免費 ] 第壹章 道可道非常道
- [ 免費 ] 第二章 花非花霧非霧
- [ 免費 ] 第三章 朱粉樓上紅袖招 ...
- [ 免費 ] 第四章 白日雄兵天上來 ...
- [ 免費 ] 第五章 錦官城
- [ 免費 ] 第六章 峨眉秀
- [ 免費 ] 第壹章 殺意和招募
- [ 免費 ] 第二章 王宮歌舞石城血 ...
- [ 免費 ] 第三章 襄王夢醒,虎帳議兵 ...
- [ 免費 ] 第四章 同仇敵愾戰雲急 ...
- [ 免費 ] 第五章 輕舟南行嘉定州 ...
- [ 免費 ] 第六章 月下試劍聞秘辛 ...
- [ 免費 ] 第壹章 喪家之犬嗟何及 ...
- [ 免費 ] 第二章 似曾相識燕歸來? ...
- [ 免費 ] 第三章 兩難決斷壹念間 ...
- [ 免費 ] 第四章 暗夜阻截血紛紛 ...
- [ 免費 ] 第五章 寶劍鋒自磨礪出 ...
- [ 免費 ] 第六章 蜀江水碧蜀山青 ...
- [ 免費 ] 第壹章 劍閣崢嶸而崔巍 ...
- [ 免費 ] 第二章 足窮幽險入窮荒 ...
- [ 免費 ] 第三章 淒風冷雨夜(上) ...
- [ 免費 ] 第四章 淒風冷雨夜(中) ...
- [ 免費 ] 第五章 淒風冷雨夜(下) ...
- [ 免費 ] 第六章 命懸壹線險戰苦 ...
- [ 免費 ] 第壹章 熱湯泉水療傷日 ...
- [ 免費 ] 第二章 細雨騎驢走河隴 ...
- [ 免費 ] 第三章 內患危機匿伏矣 ...
- [ 免費 ] 第四章 外敵內鬼何足懼? ...
- [ 免費 ] 第五章 蚌病成珠孕靈機 ...
- [ 免費 ] 第六章 密謀顛覆奔波忙 ...
- [ 免費 ] 第壹章 鬼影幢幢 對玩具空自疑 ...
- [ 免費 ] 第二章 此間爭鋒 知誰是後來黃 ...
- [ 免費 ] 第三章 群虎競食 奈何鬼府網罟 ...
- [ 免費 ] 第四章 騙局詭詐 弄假成真啼笑 ...
- [ 免費 ] 第五章 石炭黑黑 鼓噪洶洶箭矢 ...
- [ 免費 ] 第六章 熊熊烈火 壹片殘陽流盡 ...
- [ 免費 ] 第壹章 局中有局 殘局重整失顏 ...
- [ 免費 ] 第二章 初窺端倪 無心插柳得助 ...
- [ 免費 ] 第三章 前世今生 滿堂儒冠論均 ...
- [ 免費 ] 第四章治民理政 分權集權再更 ...
- [ 免費 ] 第五章 治民理政 分權集權再更 ...
- [ 免費 ] 第六章 急遣救兵 綁架勒索有隱 ...
- [ 免費 ] 第壹章 六盤觀獵 中軍牙帳理政 ...
- [ 免費 ] 第二章 水迢路遙 風水大師走南 ...
- [ 免費 ] 第三章 蓮葉田田 偷得浮生數日 ...
- [ 免費 ] 第四章 用兵布勢 簫音細細催蠱 ...
- [ 免費 ] 第五章 百折不撓 歷劫難色心勃 ...
- [ 免費 ] 第六章 風水堪輿 有益經世致用 ...
- [ 免費 ] 第壹章 迂回出奇兵 撫劍難抉擇 ...
- [ 免費 ] 第二章 金州碧血多 祥雲春光媚 ...
- [ 免費 ] 第三章 射獵盡興歸 兵臨合州城 ...
- [ 免費 ] 第四章雙修作鼎爐 桃源可問津 ...
- [ 免費 ] 第五章 對坐論律例 問對藏隱秘 ...
- [ 免費 ] 第六章 琴音淡綠痕 月兒膝上嬌 ...
- [ 免費 ] 第壹章 西苑聽政 良臣上疏廣屯 ...
- [ 免費 ] 第二章鸞鳳和鳴 數語香艷間彌 ...
- [ 免費 ] 第三章 金針離體 放眼於萬裏之 ...
- [ 免費 ] 第四章 只欠東風 洛陽烽火連天 ...
- [ 免費 ] 第五章 豪情天縱 碧海橫行圖遠 ...
- [ 免費 ] 第六章 秣馬欽州 清都世子探虛 ...
- [ 免費 ] 第壹章 猛犬與美人 羊羔在虎口 ...
- [ 免費 ] 第二章 國事與家事 未雨預綢繆 ...
- [ 免費 ] 第三章 弄潮兒向潮頭立,芙蓉帳 ...
- [ 免費 ] 第四章 壹夜芙蓉紅淚多,鴛鴦 ...
- [ 免費 ] 第五章 鬧分歧反客為主,暗爭 ...
- [ 免費 ] 第六章調虎離山計連環 成都警 ...
- [ 免費 ] 第壹章 烽火芙蓉城 不眠同此夜 ...
- [ 免費 ] 第二章 戰火燎原烈 炮聲驚天猛 ...
- [ 免費 ] 第三章 破門而入時 金蟬已脫殼 ...
- [ 免費 ] 第四章 禮曹會彌勒 都督問洛陽 ...
- [ 免費 ] 第五章 縱橫滄海雄 心如鐵石堅 ...
- [ 免費 ] 第六章 破浪逐飛舟 卞莊圖刺虎 ...
- [ 免費 ] 第壹章請神容易送神難 弱肉強 ...
- [ 免費 ] 第二章秋風隔海渡扶桑 深入敵 ...
- [ 免費 ] 第三章陋室對坐談掌故 溫泉浸 ...
- [ 免費 ] 第四章裏應外合陷洛陽 星夜馳 ...
- [ 免費 ] 第五章是疑非疑軍夜行 平明喋 ...
- [ 免費 ] 第六章蕭瑟秋風今又是 袖手坐 ...
- [ 免費 ] 第壹章 定長安
- [ 免費 ] 第二章 巡崤函
- [ 免費 ] 第三章 無定河
- [ 免費 ] 第四章 戰再敗
- [ 免費 ] 第五章 榆林塞
- [ 免費 ] 第六章 戰局終
- [ 免費 ] 第壹章 渭水夜宴 談笑之間定長 ...
- [ 免費 ] 第二章 夜闌議政 欲閑偏驚急訊 ...
- [ 免費 ] 第三章 太行追獵 樹上艷屍高高 ...
- [ 免費 ] 第四章 雪裏追蹤 裸奔驚艷殺機 ...
- [ 免費 ] 第五章 苦戰幸生 雪地宿營對嬋 ...
- [ 免費 ] 第六章 伴君幽獨 濃艷壹技細看 ...
- [ 免費 ] 第壹章 困守絕崖 可惜壹桌好酒 ...
- [ 免費 ] 第二章 火中取粟 荒丘雪舞血花 ...
- [ 免費 ] 第三章 戰罷幹戈 葡萄酒染醉顏 ...
- [ 免費 ] 第四章 風雪歸途 強敵突襲如夢 ...
- [ 免費 ] 第五章 駐帳蒲津 鶯語夜話人和 ...
- [ 免費 ] 第六章 踏雪尋梅 幽院獨行錯 ...
- [ 免費 ] 第六章 踏雪尋梅 幽院獨行錯偷 ...
- [ 免費 ] 第壹章 戈壁塵煙起 將軍夜擁旄 ...
- [ 免費 ] 第二章 聚將議奇襲 擒賊謀擒王 ...
- [ 免費 ] 第三章 落日浸寒漪 更闌眠紅帳 ...
- [ 免費 ] 第四章 美酒待遠客 坐談說‘實 ...
- [ 免費 ] 第五章 銜杯笑語頻 南征已在弦 ...
- [ 免費 ] 第六章 私語口脂香 調情欲銷魂 ...
- [ 免費 ] 第壹章 破襲哈密傳捷報 年末述 ...
- [ 免費 ] 第二章打馬吊無聲落葉 迎親事 ...
- [ 免費 ] 第三章民氣激揚翼僥幸 師徒相 ...
- [ 免費 ] 第四章眾尼西行因詐術 雷大雨 ...
- [ 免費 ] 第五章大軍遠征雲之南 秘諜閑 ...
- [ 免費 ] 第六章 白石江畔鏖戰急 行轅院 ...
- [ 免費 ] 第壹章少年營月旦點評 福利會 ...
- [ 免費 ] 第二章說‘保險’效法西洋 遷 ...
- [ 免費 ] 第三章臘月八袍澤齊聚 祭英雄 ...
- [ 免費 ] 第四章 都督破舊立新規 國公 ...
- [ 免費 ] 第四章 都督破舊立新規 國公 ...
- [ 免費 ] 第五章日暮鄉關何處是? 煙波 ...
- [ 免費 ] 第六章綠袖壹襲水雲間 山高路 ...
- [ 免費 ] 第壹章 懵懂不識處境惡 心情 ...
- [ 免費 ] 第二章 伊人如鴻飛杳杳 重返 ...
- [ 免費 ] 第二章 伊人如鴻飛杳杳 重返帝 ...
- [ 免費 ] 第二章 伊人如鴻飛杳杳 重返帝 ...
- [ 免費 ] 第三章 婚禮吉期賀新郎 巡海 ...
- [ 免費 ] 第四章 初識野性女海盜 心魔 ...
- [ 免費 ] 第五章 翡翠重逢續前緣 姐妹 ...
- [ 免費 ] 第六章 合巹之日歡同樂 雕闌此 ...
- [ 免費 ] 第壹章 明知是禍躲不過 ...
- [ 免費 ] 第二章 天下熙熙皆為利 ...
- [ 免費 ] 第三章 集議決策起爭端 ...
- [ 免費 ] 第四章 露濃花瘦汗濕衣 ...
- [ 免費 ] 第五章 密雲蓄雨風來急 ...
- [ 免費 ] 第六章 輕車歸途情繾綣 ...
- [ 免費 ] 第壹章 正月初壹的火
- [ 免費 ] 第二章 私語閑言
- [ 免費 ] 第三章 正月初五
- [ 免費 ] 第四章 元宵湯圓
- [ 免費 ] 第五章 元宵夜的暗殺
- [ 免費 ] 第六章 霜華如水照何人 ?[-] ...
- [ 免費 ] 第壹章 戰雲南
- [ 免費 ] 第二章 逼人瘋
- [ 免費 ] 第三章 逃婚記
- [ 免費 ] 第四章 破城計
- [ 免費 ] 第五章 殺破城
- [ 免費 ] 第六章 天亡我?
- [ 免費 ] 第壹章 春之味
- [ 免費 ] 第二章 春之潮
- [ 免費 ] 第三章 春之訊
- [ 免費 ] 第四章 春之醉(上節) ...
- [ 免費 ] 第四章 春之醉(中節) ...
- [ 免費 ] 第四章 春之醉(下節)(刪改版 ...
- [ 免費 ] 第五章 春之客
- [ 免費 ] 第六章 春之煞
- [ 免費 ] 第壹章 和為貴
- [ 免費 ] 第二章 回馬槍
- [ 免費 ] 第三章 折花令
- [ 免費 ] 第四章 玉之瑕
- [ 免費 ] 第五章 顛狂心
- [ 免費 ] 第六章 玉合歡
- [ 免費 ] 第壹章 千面玉狐
- [ 免費 ] 第二章 溺水滇池
- [ 免費 ] 第三章 孫家侍女
- [ 免費 ] 第四章 借刀殺人
- [ 免費 ] 第五章 煮茶爭鋒
- [ 免費 ] 第六章 了猶未了
- [ 免費 ] 第壹章 漢水烽煙
- [ 免費 ] 第二章 好整以暇
- [ 免費 ] 第三章 宜綠閑話
- [ 免費 ] 第四章 糧中有毒
- [ 免費 ] 第五章 白衣軟肋
- [ 免費 ] 第六章 息兵渡江(上) ...
- [ 免費 ] 第六章 息兵渡江(中) ...
- [ 免費 ] 第六章 息兵渡江(下) ...
- [ 免費 ] 第壹章 泰山將至
- [ 免費 ] 第二章 閨怨陰殺
- [ 免費 ] 第三章 滅絕之令
- [ 免費 ] 第四章 午後陽光
- [ 免費 ] 第五章 爭利血洗
- [ 免費 ] 第六章 應承之‘事’
- [ 免費 ] 第壹章 五月初壹
- [ 免費 ] 第二章 父子之戰
- [ 免費 ] 第三章 大婚之日
- [ 免費 ] 第四章 鞭刑調教(上) ...
- [ 免費 ] 第四章 鞭刑調教(下) ...
- [ 免費 ] 第五章 不鹹不淡
- [ 免費 ] 第六章 胸有成竹
- [ 免費 ] 第壹章 雲南人選
- [ 免費 ] 第二章 夜宴偷情
- [ 免費 ] 第三章十步芳草
- [ 免費 ] 第四章 吃喝二事
- [ 免費 ] 第五章 天師到訪
- [ 免費 ] 第六章 蝗蟲•;煩惱 ...
- [ 免費 ] 第壹章 冰縠凝霜
- [ 免費 ] 第二章 藍田種玉
- [ 免費 ] 第三章 伯顏西來
- [ 免費 ] 第四章 別扭夫妻
- [ 免費 ] 第五章 五大錢莊
- [ 免費 ] 第六章 亂世圖存(壹) ...
- [ 免費 ] 第六章 亂世圖存(二) ...
- [ 免費 ] 第六章 亂世圖存(三) ...
- [ 免費 ] 第六章 亂世圖存(四) ...
- [ 免費 ] 第壹章(壹) 駟馬獵獵 暗戰無 ...
- [ 免費 ] 第壹章(二) 微服潛行 顏如舜 ...
- [ 免費 ] 第二章(壹)狂飆殷雷 震驚百 ...
- [ 免費 ] 第二章(二) 駕彼四牡 有女同 ...
- [ 免費 ] 第三章 巧笑倩兮 碩人其頎 ...
- [ 免費 ] 第四章(壹)張網以待 誰為黃 ...
- [ 免費 ] 第四章(二)張網以待 誰為黃 ...
- [ 免費 ] 第五章 遠客來矣,維風及雨? ...
- [ 免費 ] 第六章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
- [ 免費 ] 第壹章 侃侃論政 詭譎危機 ...
- [ 免費 ] 第二章 刀鋒搏殺 血戰何府 ( ...
- [ 免費 ] 第二章 刀鋒搏殺 血戰何府(二 ...
- [ 免費 ] 第二章 刀鋒搏殺 血戰何府(三 ...
- [ 免費 ] 第二章 刀鋒搏殺 血戰何府(四 ...
- [ 免費 ] 第二章 刀鋒搏殺 血戰何府(五) ...
- [ 免費 ] 第三章 紅燭影回 世態炎涼(壹 ...
- [ 免費 ] 第三章 紅燭影回 世態炎涼(二 ...
- [ 免費 ] 第三章 紅燭影回 世態炎涼(三) ...
- [ 免費 ] 第三章 紅燭影回 世態炎涼(四) ...
- [ 免費 ] 第四章 玉潤花嬌 殺機鬼藏(壹 ...
- [ 免費 ] 第四章 玉潤花嬌 殺機鬼藏(二) ...
- [ 免費 ] 第四章 玉潤花嬌 殺機鬼藏(三 ...
- [ 免費 ] 第五章 兵要地誌 策議蠶食(壹 ...
- [ 免費 ] 第五章 兵要地誌 策議蠶食(二 ...
- [ 免費 ] 第六章(壹)鵪鶉賭鬥 夜來寒 ...
- [ 免費 ] 第六章(二) 女煞雌威 戮之如 ...
- [ 免費 ] 第六章(三)刑訊有術 玉蟾道書 ...
- [ 免費 ] 第六章(四) 拂曉突襲 騰空媚 ...
- [ 免費 ] 第六章(五)香溪野合 秘府探 ...
- [ 免費 ] 第六章(六) 百蝶穿花 逍遙北返 ...
- [ 免費 ] 第壹章 吉囊回光 鬼斧雷槍 ...
- [ 免費 ] 第二章 趁夜突襲 血流成河 ...
- [ 免費 ] 第三章 懸紅殺人 趁火打劫 ...
- [ 免費 ] 第四章 塞北秋獵 渡河初戰 ...
- [ 免費 ] 第五章 祭奠汗陵 敵友之間 ...
- [ 免費 ] 第六章 大雪弓刀 截殺於途(壹 ...
- [ 免費 ] 第六章大雪弓刀 截殺於途(二 ...
- [ 免費 ] 第六章 大雪弓刀 截殺於途(三 ...
- [ 免費 ] 第壹章 立城
- [ 免費 ] 第二章 哥薩克人
- [ 免費 ] 第三章 人質
- [ 免費 ] 第四章 女皇之盟
- [ 免費 ] 第五章 師還
- [ 免費 ] 第六章 酒宴
- [ 免費 ] 第壹章 過關
- [ 免費 ] 第二章 門神與土財主
- [ 免費 ] 第三章 仙霞關與福州城(壹) ...
- [ 免費 ] 第三章 仙霞關與福州城(二) ...
- [ 免費 ] 第四章 逃亡的烏鴉
- [ 免費 ] 第五章 見我生財與天下無諜 ...
- [ 免費 ] 第六章 安得此身生羽翼,與君 ...
- [ 免費 ] 第壹章 閑說齋名是止戈 ...
- [ 免費 ] 第二章 諜中諜
- [ 免費 ] 第三章 戰爭已經開始,但是沒 ...
- [ 免費 ] 第四章 寶刀賜烈士
- [ 免費 ] 第五章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
- [ 免費 ] 第六章 官身不自由
- [ 免費 ] 第壹章 微服不私訪
- [ 免費 ] 第二章 賊老天
- [ 免費 ] 第三章 晴時買傘 旱時作舟 ...
- [ 免費 ] 第四章 擄掠事件
- [ 免費 ] 第五章 無名氏
- [ 免費 ] 第六章 戒律會
- [ 免費 ] 第壹章 平虜侯令
- [ 免費 ] 第二章 前途多艱
- [ 免費 ] 第三章 道不同
- [ 免費 ] 第四章 地火
- [ 免費 ] 第五章 大風起兮
- [ 免費 ] 第六章 月下刀光寒
- [ 免費 ] 第壹章 商機
- [ 免費 ] 第二章 說書夜(上)
- [ 免費 ] 第二章 說書夜(下)
- [ 免費 ] 第三章 交換
- [ 免費 ] 第四章 元老院修行師範 ...
- [ 免費 ] 第五章 節外生枝
- [ 免費 ] 第六章 興亡與我何幹? ...
- [ 免費 ] 第壹章 籌算
- [ 免費 ] 第二章 借口
- [ 免費 ] 第三章 湯泉浴火(上) ...
- [ 免費 ] 第三章 湯泉浴火(下) ...
- [ 免費 ] 第四章 陽乖序亂,陰以待逆 ...
- [ 免費 ] 第五章 收網
- [ 免費 ] 第六章 潛襲中的潛襲
- [ 免費 ] 第壹章 破
- [ 免費 ] 第二章 覆巢
- [ 免費 ] 第三章 (上)骨鯁在喉 ...
- [ 免費 ] 第三章 (下)幻夢藏奸 ...
- [ 免費 ] 第四章 驚變
- [ 免費 ] 第五章 餌
- [ 免費 ] 第六章 亂戰
- [ 免費 ] 第壹章 凡人的煩惱
- [ 免費 ] 第二章 霸王硬上弓(上) ...
- [ 免費 ] 第二章 霸王硬上弓(下) ...
- [ 免費 ] 第三章 京師的那潭渾水 ...
- [ 免費 ] 第四章 風雨落幽燕(壹) ...
- [ 免費 ] 第四章 風雨落幽燕(二) ...
- [ 免費 ] 第四章 風雨落幽燕(三) ...
- [ 免費 ] 第五章 帝京變亂的日子(壹) ...
- [ 免費 ] 第五章 帝京變亂的日子(二) ...
- [ 免費 ] 第六章 天崩地裂(壹) ...
- [ 免費 ] 第六章 天崩地裂(二) ...
- [ 免費 ] 第壹章 獵莊
- [ 免費 ] 第二章 薦書
- [ 免費 ] 第三章 投宿
- [ 免費 ] 第四章 糧草
- [ 免費 ] 第五章 審計
- [ 免費 ] 第六章 教主?
- [ 免費 ] 第壹章 放血
- [ 免費 ] 第二章 內戰
- [ 免費 ] 第三章 雷霆
- [ 免費 ] 第四章 蔥嶺
- [ 免費 ] 第五章 烈士
- [ 免費 ] 第六章 陰雲
- [ 免費 ] 第壹章 大閱禮
- [ 免費 ] 第二章 大潰敗
- [ 免費 ] 第三章 燒炭
- [ 免費 ] 第四章 弱肉強食
- [ 免費 ] 第五章 吏治與糧政
- [ 免費 ] 第六章 決戰
- [ 免費 ] 第壹章 背包商、神秘人和狼群 ...
- [ 免費 ] 第二章 夜歸人
- [ 免費 ] 第三章 論劍黃河濱(上) ...
- [ 免費 ] 第三章 論劍黃河濱(下) ...
- [ 免費 ] 第四章 逆轉
- [ 免費 ] 第五章 弓如霹靂弦驚
- [ 免費 ] 第六章 小人物 (上) ...
- [ 免費 ] 第六章 小人物(下)
- [ 免費 ] 第六章 戒律會)
- [ 免費 ] 第壹章 河中之議
- [ 免費 ] 第三章 步兵軍團 等章) ...
- [ 免費 ] 第二章 嶺南亂起
- [ 免費 ] 第三章 司民之牧(上) ...
- [ 免費 ] 第壹章)
- [ 免費 ] 第二章 薦書)此前卻是自蜀中 ...
- [ 免費 ] 第三章 司民之牧(下) ...
- [ 免費 ] 第四章 襲擊
- [ 免費 ] 第四章),程沂在當年平虜侯成 ...
- [ 免費 ] 第五章 關於憤懣與縣政(上) ...
- [ 免費 ] 第二章 等等章節)
- [ 免費 ] 第五章(下)
- [ 免費 ] 第六章 箭在弦
- [ 免費 ] 第壹章 行轅
- [ 免費 ] 第二章 和爾木斯?和爾木斯!( ...
- [ 免費 ] 第二章 等),自然知道‘天寶 ...
- [ 免費 ] 第二章 和爾木斯?和爾木斯!( ...
- [ 免費 ] 第三章 父與子(上)
- [ 免費 ] 第三章 父與子(下)
- [ 免費 ] 第四章 二三事
- [ 免費 ] 第五章 家/國
- [ 免費 ] 第六章 考試近
- [ 免費 ] 第壹章 風起滇之南
- [ 免費 ] 第六章 月下刀光寒)
- [ 免費 ] 第二章 大紅燈籠(上) ...
- [ 免費 ] 第五章 等)
- [ 免費 ] 第二章 大紅燈籠(下) ...
- [ 免費 ] 第三章 鐵匠木匠將軍令 ...
- [ 免費 ] 第四章 陰影中的……
- [ 免費 ] 第五章 亂
- [ 免費 ] 第六章 裂土封疆
- [ 免費 ] 第壹章 戰局.移民 (上) ...
- [ 免費 ] 第壹章 戰局.移民 (下) ...
- [ 免費 ] 第壹章)
- [ 免費 ] 第二章 軍議與練兵
- [ 免費 ] 第三章 中間人與隔墻耳 ...
- [ 免費 ] 第四章(壹)荒淫怠政? ...
- [ 免費 ] 第四章(二)給養唯艱 ...
- [ 免費 ] 第五章 中原轉折(壹)
- [ 免費 ] 第五章 中原轉折(二)
- [ 免費 ] 第六章(壹) 遠遊之前
- [ 免費 ] 第六章(二)‘佞佛’和‘佞道 ...
- [ 免費 ] 第六章(三)牌局閑話 ...
- [ 免費 ] 第六章(四)代耕互助社 ...
- [ 免費 ] 第六章(五)公爺的無奈之處 ...
- [ 免費 ] 第六章 ( 六 )月圓月升 ...
- [ 免費 ] 第六章(七)秋天
- [ 免費 ] 第六章(八)婚姻禮成
- [ 免費 ] 第六章(九)秋風起兮天下寒 ...
- [ 免費 ] 第壹章亂局中的諜來諜往(壹) ...
- [ 免費 ] 第壹章亂局中的諜來諜往(二) ...
- [ 免費 ] 第二章 四海通商
- [ 免費 ] 第三章 福音、跋涉與異動 ...
- [ 免費 ] 第四章 風雨欲來,微服出遊 ...
- [ 免費 ] 第五章 南方的清剿
- [ 免費 ] 第六章(壹) 必爭之地
- [ 免費 ] 第六章(二)會戰兩河 ...
- [ 免費 ] 第六章(三)潼關!潼關! ...
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壹章)
2025-6-14 20:28
鄭佛兒得知這屯墾學校裏頭管吃管住不要錢,壹咬牙便去‘官辦屯墾學校’應征做了學生,準備學成之後做個幾年候補‘衙役’,總歸有機會吃上公家飯——‘屯長’、‘保正’之類,以鄭佛兒當時的理解,便類似於官府的衙役,大小也算個官兒。
鄭佛兒後來便隨軍西征,被官府分在河中直隸府地面做了壹個‘屯長’,這個屯便是以他鄭佛兒的姓氏冠名為‘鄭官屯’,湖廣的父母兄弟姐妹等親族,也被他陸續接到了西域河中府入籍落戶。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txt電子書下載
鄭佛兒當年孤身闖四川,是因為他夢想過上良田千頃牛羊無數仆從如雲的地主生活。現在僅他壹個人在鄭官屯轄地之內,就有著壹個包括了數千畝田地、草場的莊園,養著馬牛羊駝驢騾等各種牲畜,使喚著成百上千的奴隸,還開著壹些手工作坊,可謂是心想事成。如果是在湖廣地方,他鄭屯長這點家業雖然算不上大地主,也足以稱為壹方首富。只不過西域五谷豐饒的土地、水草肥美的草場多半是官地官牧,現都是由‘總商’包租,諸如耕種牧養和納糧交租,壹般百姓是無緣染指的;象鄭佛兒的莊園。現在所耕種的田地,全是開荒地,地力都有些瘠薄,壹畝地麥黍收成不過壹石五六鬥,差壹點的壹石都不到,雖然說那些地有的免了起頭三年稅糧,有的免了五年稅糧,甚至有免了十年稅糧的開荒地,但鄭佛兒私人莊園中能夠積攢下來的糧食,到現在也不會有很多;莊園的牲畜是半圈養放牧,頭幾年也是雞飛狗跳手忙腳亂。現在才算是穩定下來,有了些進項收益;歸總壹句話,好日子從此開了頭,以後有盼頭。
類似於‘鄭官屯’,這種由移民和奴隸形成的‘屯’在西域已經遍地開花,其實就是兵民合壹、屯墾群牧工商和駐地守禦合壹的準軍事屯社組織,入則為民,出則為兵,官方對‘屯’的管轄眼下也是相當嚴密的,象屯長、保正這樣效力於西北幕府的半官方底層‘屯官’,即便沒有上級直屬長官的征召命令,也都有義務定期到縣城向所屬屯務長官述職。當然‘屯官’如果實在受不了官方的管束,也可以卸任交接,另外討個‘世襲開疆宣撫使’、‘世襲武勛招討使’之類的‘委任狀’,去那等窮荒邊陲、他國地界‘駐屯’,靠壹刀壹槍的勇力開辟占領壹塊土地並歸屬自己所有。在宣誓效忠平虜侯並盡到其臣服貢賦、從征作戰等義務的前提下,他們可以得到平虜侯賜予的正式封號、爵位、官銜等等,從而將其從奴隸商人手裏買來或自己俘獲的人口,在其占領地設置壹處世襲采邑(民間俗稱‘邊屯’,官方則稱為‘鄉邑’、‘縣邑’或‘州邑’,以便與西北幕府直接統轄的其他州縣區別),較大的世襲采邑可以修建城郭要塞,小的世襲采邑可以修建‘屯鎮’或者‘屯堡’等堡寨,通過戰鬥俘獲或者出錢買來的男女奴隸人口,凡是會耕種者安排從事農耕,會放牧者安排從事圈牧放養,有技藝者則令其從事手工業等等。這些世襲采邑的奴隸采邑戶,壹方面要向采邑貴族交納地租,另外還須向西北幕府交納稅課,並向平虜侯府交納‘貢賦’;城市、屯鎮中的工商稅課,除了西北幕府規定交納的少數稅課之外,其他均歸采邑的世襲貴族所有;這種實領或者半實領的世襲采邑,其官吏除了西北幕府所規定的壹兩位首領官以外,都由采邑貴族委派。世襲采邑的奴隸戶口(采邑戶), 壹面依附其本主,壹面依附西北幕府和平虜侯府。
鄭佛兒現在只做到‘屯長’,卻擁有自己的莊園塢堡。屬於他名下的田地和草場已經讓他很滿足眼下的地主老財生活,自然不會再有進取世襲采邑的野心。他覺得只需要管好‘鄭官屯’所轄地界,對上盡職效忠,對下盡量公平公正履職盡責就好了。
不過,這次到縣城述職,他得到壹個不知道是好還是壞的消息:從今年開始,除了那些世襲采邑貴族必須將其適齡子女送往平虜侯府做伴當扈從之外,文官幕僚、軍中將士和底層屯官也可以將其適齡子女送往平虜侯府做伴當扈從。
這個消息意味著什麽,縣城的直屬長官也給所有的述職屯官透露了壹些,其中的‘質子’意味固然是隱約有壹點,但主要還是著眼於為西北的將來作育培養新血。直屬的長官還說了,送了去做伴當隨扈的子侄,文才武藝都有平虜侯府的名師高人專門指導點撥,屯官們便不需要為家中子侄輩的學業操太多的心,許多開銷都是由平虜侯包圓了。因此,將自家的子侄送到平虜侯府做伴當,方方面面的好處很是不少,壹是這種效忠臣服於平虜侯的政治秩序將更加穩固,上對下和下對上都會比較放心;二是子侄輩的文武學業有了平虜侯府負擔其中許多開銷,底層屯官對後輩的教誨培養便可以節省許多精力財力,從此也便少了許多後顧之憂;三是子侄們在平虜侯眼前左右侍奉,壹旦能得到平虜侯等貴人的青睞,飛黃騰達也不過是壹兩句話的工夫,這樣的機會豈能錯過?
反正後繼有人,家業自然興旺發達,世世不衰,這是壹定不易之理,哪怕是不識字的大老粗都知道這個理,何況是這些略通文墨的屯官們呢?他們當初都在屯墾學校裏,被硬逼著學曉了識數和簡單算術,也會默背抄寫《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又能將蒙學裏頭的《昔時賢文》熟背默寫,怎麽著也算是小半個讀書人了,壹些簡單的官方文牘還是可以應付壹氣的,至於象鄭佛兒這樣本來就粗通文墨的,更是屯官當中的佼佼者了。
但這個事,畢竟牽扯不小,關系到家中子侄將來的前程和家族的興旺,鄭佛兒還是覺得要合家聚齊商議後再定下來比較妥當。
因此,述職完畢,鄭佛兒甚至等不及的就往回趕,也虧得如今的河中府道路安靖,他又自恃己身武勇,打小就學過壹些拳腳把勢,在西北屯墾學校更又多學了不少槍棒武藝,等閑三五個壯漢不能近他的身,所以來回都是孤身獨行,竟是趕在大晌午後的未正時辰就往回返,只是縣城到屯子的路途遠,再怎麽趕路,也得露宿壹宿才能回到鄭官屯了。
鄭佛兒壹個人駕的大車,裝滿了在縣城順便采買的日用雜貨,趕路也不很快。
過了關家鋪,鄭佛兒卻遙見前頭有壹行人馬也在趕路,心想:這些人莫是錯過了宿頭罷?
再走近些,他略略打量,卻是壹幫十幾個伴當隨從,護持著壹家大小的樣子。這些人雄壯魁梧,氣宇剽悍,挾弓箭,佩刀劍,其中還有背負飛槍鏢囊的,又帶著壹群兇猛獵犬,架了鷹隼,幾個隨從馬後還牽著幾匹馬,馱滿雞兔沙狐野豬之類野味。
興許是帶著家裏小孩兒出來踏青射獵,遊玩耍子的大戶人家。
鄭佛兒想到,他見裏頭那家子人有兩個戴著帷帽胡服著靴的妖嬈婦人,衣飾雖然簡單而不奢華,裁剪卻見氣度,女紅針線也精致,衣料亦是上佳的綢緞;又有壹個男孩,壹個女孩,小小年紀,看那騎術卻是熟練,身上也是上下錦繡,絕不可能是平常人家;那年青男子好生雄武高大,倒是娶的好渾家,而且也未見許多行李,不類遠道而來的行旅客商,想必就是河中府遠近地面的人家,必定是個大門第。
鄭佛兒卻也不在意,反正他這鄭官屯的大車有巡捕營核準發給的銘牌和車旗——‘鄭官屯○伍’,別人遠遠壹看就知道他這大車的底細,倒也不會過分戒備。
等大車趕上那壹家人,鄭佛兒甚至還與那壹家人墜在隊尾的大管家搭白,壹問壹答地聊了幾句天氣陰晴、道路遠近、何處投宿、田地收成的閑話,打個哈哈,拱手超車而去,卻也不甚理會這路遇的壹家子,卻不知這家人正在後頭說道壹些與他這鄭官屯稍微有點關聯的閑篇兒,就是知道了,估計他也不會在意了。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電子書下載
這壹家子人,確實如鄭佛兒所猜想的那樣,是趁著春夏之交,河中氣候涼熱適宜的當口出來踏青射獵,遊玩耍子的。但這壹家子人,身分卻非同小可:那年青男子便是西北‘平虜侯’雷瑾,而兩位戴帷帽的妖嬈婦人,壹位是綠痕,壹位則是阿羅斯公主、女大公瑪麗雅,而男孩則是綠痕生的兒子雷洹,女孩則是紫綃生的女兒雷湄,平虜侯的子女起名都從水旁,諸如‘泓洹浣濠瀚灝澮滸淮洪渙涵湟浚灤濟漸梁洛瀾瀝潞泠濼澧濂瀧’等等。
雷瑾微服出行踏青射獵,雖然是‘輕車簡從’,這前後警蹕護衛的人手卻也不只鄭佛兒看到的那十幾個伴當隨從。再者說了,雷瑾、綠痕、瑪麗雅,又有哪壹個不是殺人如割草的高手?
“方才那人,便是屯社的移民吧?”瑪麗雅壹眼瞥見雷洹欲言又止,知道小孩兒有些好奇,但又畏懼父親雷瑾的威嚴而不敢隨便發問,眼睛壹轉便故意問雷瑾,她猜雷洹想問的必定是那大車上插的車旗兒。
“鄭官屯的移民,唔——那人應該是從縣上述職返回的屯長或保正,他說明天就可到家,大車跑得有些慢,所去應該不是太遠。”雷瑾隨口答道,“那人壹身骨肉魁碩壯實,目光炯炯有神,說話時斂氣含勁,中氣十足,似乎練過護身硬功;揮舞鞭桿時攔拿圈法嫻熟,暗合六合大槍法度;壹雙手掌更是粗大異於常人,肌膚卻光滑細膩,幾乎見不到什麽胼胝老繭,明顯是依著鐵砂掌真傳藥功方子苦練有成的模樣;臂腕筋肉虬突,猶如鋼絲絞纏,可能還兼修了少林鐵掌功、鐵臂功、鷹爪功之類的硬功以及少林軟玄(腕)功、綿掌之類的陰手功法,成就還都不俗;呵呵,看這個樣子,再加上大車上的車旗、銘牌都是‘鄭官屯’標誌,那人十有八九是從我西北屯墾學校出身的屯官。再聽他說話口音,湖廣官話中偶爾還夾帶著少許山西話口音,想必他祖上也是國朝初年從山西遷移到湖廣的移民,只是居然又從湖廣遷移到我西域的河中府,倒是——”
雷瑾說到這便未往下再說,瑪麗雅嫣然笑道:“聽說國初太祖遷山西澤州、潞州無田之民,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閑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賦役三年,戶給寶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嗯,立村屯田可以自便,不過仍需驗丁給田,冒名多占就要處罰了。”雷瑾笑說道。
綠痕這時也湊趣答話道:“遷民分屯之地,河北(註:黃河以北)州縣多以‘屯’分裏甲。移民村屯差不多都是叫‘某某屯’。象什麽小楊官屯,張官屯,高官屯,董官屯,牛官屯,徐官屯,尚官屯,皆為某官某員奉旨督遷山西移民到此屯田建成的村屯。”
“確實如此。”
雷瑾頷首贊同,“國朝太祖皇帝幹別的或者不行,移民卻絕對是個中行家裏手。當年太祖還在紅巾軍、小明王旗下的時候,就在江淮流寇那裏學了不止壹手的裹挾平民之術。到太祖自立為吳王,前後數年又與人先後爭雄於江淮,在江淮壹帶來回移民,那還只是壹次幾千幾萬的移民,規模不大。等到北伐底定中原,太祖屢次移江南富民充實金陵、北平,又因各地人口雕敝,屢次下令從戰亂較少人口較多的山西向外地移民,充實各地。
諸般種種,皆事出有因。
某些躲在書齋裏讀春秋的大人先生們,其生也晚,不識當年為政之艱難,並不理解太祖那時為啥要移民,其實原因簡單得很,不過是這樣最適宜鞏固新朝統治罷了。
比如遷移富民充實京師、北平,壹則利於集中看管並以之充實賦役,壹則打斷各地鄉族勢力的根底,天下自然太平,也就少了許多亂子。當然,太祖皇帝壹直對當年打天下時,江浙富民的不恭順耿耿於懷並深懷戒心,報復壹下的意思肯定也是有的,嘿嘿。”
馬踏碎步,輕馳向前。
雷瑾顯然有借著當下這個話頭教誨子女的意思,與瑪麗雅、綠痕的對話亦是說給雷洹、雷湄兄妹聽的。所以評論國朝太祖的施政大體上還算不偏不倚,不過言語之間對國朝太祖的不恭語氣也是明明白白,“元末天下大亂,開國定鼎之初,各地人口流散,勞力緊缺,土地荒蕪,所謂‘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裏少人煙’是也,深深威脅著新皇朝統治的穩定,國初財用極為窘迫,太祖皇帝因此下詔說‘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
當時若不移民,又能怎麽辦呢?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TXT小說下載
國初定鼎,中原之地,河南人口是壹百八十九萬壹千多口,河北人口是壹百八十九萬三千多口。而山西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於中原人口的總和。勞力緊缺,土地荒蕪,不從山西移民,又能從哪裏移民?
太宗靖難之時,山東等地方不從北軍的村落,北軍兵馬來時皆屠掠之;依附北軍的村落,南軍兵馬到時也縱兵屠掠之;山東人口亦為之大減,因此靖難之後的移民也是勢在必行。
國初定制,對北方郡縣荒蕪田地,召鄉民無田者墾辟,每戶給十五畝,另給二畝地種蔬菜,尚有余力者不限頃畝。同時皆免三年租稅。
國初,移民出發之前,官府設局駐員,發給移民憑照川資;移民到了屯田地,官府則要給田、賞鈔、編裏甲。
壹切都是為了充實勞力,增加耕地。
從窄鄉移到寬鄉,從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曠的地方,如果不是為著充實勞力,增加賦稅,從而使天下安定,統治穩定,國初太祖、太宗皇帝又何必為此多方勞神,費心費力?打天下不易,治天下又何嘗容易?”
雷瑾說到這裏,心裏倒是與國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若有戚戚焉,那些大人先生們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又如何知道當家主事的千難萬難?真真的站著說話不腰疼!
西北幕府向西域,向雲南,向緬地的大規模移民,西北朝野各方歷來就有很大爭議,異見不斷,雷瑾口中某些‘躲在書齋裏讀春秋的大人先生們’,對西北幕府,對平虜侯的激烈攻訐從未斷絕,概因大規模向外移民並不符合自古以來鎮之以靜的傳統治道。
再比如在移民途中病死餓死壹些人口,移民們自己都覺得天經地義,歸之於正常,這天底下哪年不死人呢?有什麽可驚詫的?但就是有不少‘大人先生’們‘驚詫’莫名,‘憤恨’不已,以此瑕疵大肆攻擊西北的移民和鼓勵移民之策,仿佛移民中死了壹個兩個人,天就要塌了,地就要陷了,國將不國了;亦有不少自詡公允公正的‘大人先生’們認為,象西北這樣大規模的向西域異國屯墾移民,前所未聞,官府也好,百姓也好,都是既無準備又無經驗,施政過於莽撞躁進,宜緩緩圖之,最好是斷然改弦易轍,方是利國利民之正道,實質仍然是反對西北的大規模移民屯墾和鼓勵移民屯墾。
其實要說屯墾移民的經驗和準備,在中土的朝廷和官府這方面,對移民們進行編保編甲,部勒成伍,推舉父老,上命下達,啟程之前發給憑照川資,爾後押送移民壹天走30裏、40裏,走個壹年兩年,穿州過府,到了地方授田給牛給種子等等。另外沿途官吏兵卒如何部署接應交割,籌糧、運糧、給食,彈壓騷動,各地官府的官吏差役也都有可資沿襲遵循的壹定之舊例成規。比如更番宿衛,軍士們長途跋涉,往返於邊鎮與京師之間;比如天下州縣,官吏差役年年押送充軍罪囚往返數千裏之遙;比如憲宗年間,官方遣散安置聚集在隕陽府的數十萬上百萬流民,雖然千難萬難,最後也都盡數就地安置下去;可以說中土朝廷官府應付這些事情,總是有許多舊例成案可以借鑒照搬。
而作為移民這壹方面,中土諸省平民其實對官方的那套強制移民做法並不陌生。各土各鄉的老輩子人都久經考驗,經歷過春荒、逃荒、逃難等人間慘事,經驗豐富,知道自己家該做什麽,才能不掉隊、不餓死、少患病、少出意外,俗話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百姓庶民的智慧也是無窮無盡的。
大人先生們其實也根本不在乎移民是死是活,也根本不在乎移民有沒有準備、有沒有經驗,說白了他們就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實質上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為的還是他們那個階層的既得利益。他們的號叫,他們的攻訐,都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話說在這帝制皇權時代,農耕需要勞力,人口通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某些特定時候也是不那麽重要的。囿於各種條件,這年頭移民在遷徙途中死亡的肯定有,而且數量絕不在少,不過這時代死個把人死幾個人是很正常的,人命根本不值幾個錢,千萬人的辛酸和血淚,幾代人的痛苦或美好,經風歷雨,冷眼相對,不過如此而已。
移民之政,事關壹朝的興亡存廢,又哪裏可能因為某些人的爭議和反對就中輟停止呢?任何壹個當權柄政者,都不可能聽了蒼蠅的幾聲嗡嗡,就將關乎自身存亡的大政國策撂開不理。
綠痕、瑪麗雅也知道雷瑾這是借機宣泄心裏的幾分悶氣,眼下把話說完了也就完了,該做什麽還得做什麽,她倆個當下聽著也就是了。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小說在線閱讀
鄭官屯裏趕車的師傅,被尊稱為車戶,這是河西壹帶的習慣。
車戶的地位,在移民村屯中僅次於屯長和保正,並不是誰想幹就能幹的。當車戶要手腳麻利,處事果斷,善待牲口,還要能吃苦,套車、趕車、修車、飼養照料牲口、醫治常見的幾種牲口傷病等等,都得會上那麽壹手兩手。
鄭佛兒是屯長,不過車戶活計他也全都會,所以上縣城向直屬長官述職他也不用車戶趕車,自己就壹手包辦了,這樣不但省了人力,還能順便從縣城采買捎帶壹些鄉下村屯不易買到的日用雜貨,這比騎馬要方便。
拉車的馬和騾不管有沒有靈性,處的日子長了,它就能從掌鞭車戶的聲調高低,聲音大小與吆喝次數、吆喝間隔的時間,判斷出向右或者向左的力度與幅度。
河西大車通常是由騸馬駕轅,兩匹或三匹騾馬當梢子。趕車人只要看看套繩是否繃緊,就知道哪匹馬或者騾子出工不出力,這時伸出鞭子在那頭牲口的上空甩壹朵鞭花,被警告的馬或者騾子通常會趕緊把繩套繃直,否則就得挨鞭子抽了。有的牲口性子懶,看趕車人有些懈怠,便會偷懶,眼睛的余光看到趕車人要拿鞭子時,會狡猾地立即拉直繩套,省去壹鞭之苦。天長日久,趕車人也知道了每匹牲口的脾性,但凡喜歡偷懶的牲口,其眼睛兩側便會遮上壹個物件,牲口不知道何時鞭子會落下,便也使了勁地拉車,不敢耍滑頭了。
鄭佛兒當年孤身闖蕩,在屯墾學校裏本著藝多不壓身的心態,費了老大的勁,硬是學會了騎馬、射箭、打銃、操炮、趕大車等等技藝,雖然也都是及格而已,但卻讓鄭佛兒很快成了屯裏的能人,對他樹立自身威望還是大有幫助。
晚上在路上趕了大半夜車,困了就在大車上湊合瞇了半宿,鄭佛兒第二天天剛亮就又趕著大車回到了屯子。
進了屯堡的寨門,大車從屯子中間的戲臺街上過,再折向堆放打碾的打麥場,屯裏的小孩子就跟在車後面跑,鄭佛兒樂呵呵的,也不管他們,這些孩童就是鄭官屯的未來了。
鄭官屯剛剛在這壹帶圈地築堡的時候,是很艱苦的。
且不說番胡與野獸的侵襲,當初剛剛立屯,屯裏鑿井未成,水窖、雪窖、冰窖、雨窖又未竣工,用水只能靠屯子裏的露天澇池。到了冬天,澇池常常就凝冰幹涸,屯戶便把澇池中的冰塊敲碎運回家,化成水做飯或者飲用。最後,當冰塊也沒有時,就得靠大車壹趟又壹趟的到很遠的地方去拉冰塊。冰塊碼在大車上,出太陽的天,冰塊表面融出的水,就順著芨芨草編的席笆子流下來,在地上劃出壹道壹道的水痕。鄭佛兒的趕大車技藝在立屯之初便救了急,他與屯裏另外幾位車戶,輪流帶著人去拉冰塊,可是立了大功勞,也樹立了威信。
冬天,餵養牲口的事就主要由騾馬戶擔起來。羊群每日被吆喝著走向屯外的河灘,用細小的蹄子刨去積雪,刨去積雪下面的浮土,覓食草根。牛、騾、驢、駱駝、馬這些大牲口,便都圈養起來,麥草是牲口最主要的吃食,間或餵些豆稭、谷草,給牲口們改善夥食。到了第二年春天,屯裏就得弄些豌豆,磨碾成碎粒,拌些油渣,用水泡了餵大牲口。
鄭佛兒還記得往年冬天,象囚犯壹樣圈養的牲口們,每天壹早壹晚,有兩次飲水的時間。從各家各戶的牲口圈和屯裏共有的牲口欄裏趕出來的牲口,都聚在澇池。許多背著糞筐的男孩跟在牲口後面,看那個牲口厥起尾巴,就搶著把糞筐接在牲口屁股後面,看著牲口的糞便壹骨碌壹骨碌地落在糞筐中。大牲口中,牛極配合孩子們接糞,牛壹邊拉壹邊走,步子穩實,或者就站著不動,接糞容易。而馬和騾子,便不壹定了,有時也會很配合地拉完那泡馬糞、騾糞,不高興的時候便猛地揚起後腿,給人壹蹄子,接糞就得眼疾手快了。牛羊糞便都是肥田的好東西,開荒立屯的人們,各家各戶都把牛羊糞便當寶呢。窮人家孩子早當家,大多數屯戶家子弟本質上都是勤勞勇敢的,他們就是鄭官屯將來的頂梁柱,鄭佛兒閑著沒事的時候倒也常與他們說笑,屯裏小孩子倒也還不怕他。
西北幕府治下的村寨屯堡,都編有民壯鄉兵,他們與官府正式僉派的‘僉兵’又有不同,是村寨屯堡自身組織的守禦力量,絕大部分武器和口糧都是自籌自給,會操訓練則由軍府就近指派軍士督促指導。出於支持屯墾戍守安靖地方的目的,西域地方屯堡的民壯鄉兵,其農閑會操訓練口糧可以得到長史府的錢糧補貼,核銷相當大的壹部分開銷,這是西北其他地方村寨屯堡難以享受的待遇。
鄭官屯的民壯鄉兵們每每議論,吃些甚麽才好呢?但他們除了想到會操訓練時從每日兩餐增加到每日早中晚三餐之外,訓練中間再來兩次點心之外也想不到其他什麽了。鄭官屯其實是個‘窮鄉僻壤’,主要依靠自給自足,那裏會買得到好的吃食?
恰巧鄭佛兒上縣述職,自然每次都要順便擔負采買的任務,這也是他趕著大車進城的原因,否則騎馬來回,可要比趕大車快多了。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電子書下載
鄭佛兒每次采辦回來,也都不運回倉庫,而是在打麥場上當眾公開點交再入倉庫,帳目則交付給鄉兵隊‘軍需’,這也是鄭佛兒自己想的壹個辦法,免得落下口實,錢糧上面還是小心為上——鄭佛兒常聽老人們說,‘手中無權,放屁不響;手中無錢,說話不靈’,這幾年屯官做下來,他倒也領會了這刀把子或者說印把子以及錢袋子的許多厲害,反有許多顧慮,這或者就是所謂的‘江湖越老,膽子越小’了。俗話說‘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采買吃用的人難免不落下別人猜疑,如果自個處事再不小心,壹旦遇上掰扯不清的事那就糟糕了,西北幕府行的可是軍法,別冤枉吃了小人陷害。
鄭佛兒這壹回來,屯裏慣例是敲鐘聚齊,除了下地幹活和當值守禦的,其他人都從四面八方聚到打麥場。
看到各家各戶都到的差不多齊了,便點交了采買帳目,鄭佛兒又當眾將他這次上縣述職的壹些事情說了說。
鄭官屯今年的大事與往年也差不多,就是要應付官府的‘僉兵’、徭役和交納稅糧,再就是增修、翻修水窖、雪窖等蓄水窖池,增修草料青貯窖。
通常來說,土地和勞力就是國家根本。官府要是頻繁派征徭役,不恤民力,糧食、賦稅必然大受影響,哪怕象西北這樣工商之業已經繁榮發達到壹定程度的地方,其根基仍然要依靠農耕畜牧。
徭役基本上屬於無償,而且多數時候需要服役者自備口糧或者勞役工具。勞力被派征徭役,田地就未免出現荒蕪的情形,所以西北壹般不輕派徭役,對於勞力上的缺口,西北眼下基本上是用奴隸來彌補的。西北幕府也不是說就完全不派征徭役,但比較傾向於縮減徭役的種類範圍(裏甲、均徭、雜泛)和應役者不離鄉土。只要條件允許,‘力役’‘雜役’等各項徭役,西北官府通常首選‘募役’(雇傭招募勞工服役)和‘助役’(津貼應役者)的方式,又或者完全調派官奴充役,也允許‘義役’(買田以供役者)、以銀代役(兵役除外)形式的存在,盡量不征和少征徭役,即便派征也盡可能就近服役而不使應役者遠離鄉土,以免擾民累民。歷代所謂‘輕徭薄賦’之仁政德政,如果‘薄賦’僅僅指田畝正賦的適量征收,西北幕府基本上是做到了,而‘輕徭’也能大部分做到——帝國朝廷在神宗年間施行‘壹條編’之後,百姓本來可以納銀代役,但是西北征派的徭役中,兵役壹項卻是按戶籍逐戶僉派,不準納銀代役,違者治以重罪。西北現在的徭役,其實就是以‘僉兵’兵役為主,而且西北‘僉兵’也有數量較少的‘月糧’供給,若調遣則有‘行糧’和壹些津貼,並非完全的無償,應該算是‘助役’的壹種。
僉兵和徭役,對鄭官屯的移民屯戶而言,自然是大事。自古以來納糧當差,中土百姓對徭役派征的畏懼程度,遠遠超過納糧交稅,但有風吹草動,心裏就惶惶不安。
鄭佛兒將他在縣城打聽到的情形,跟屯裏的老少爺們通說了壹遍,也花了許多的時間,屯戶們聽說今年僉兵、徭役的變動不大,都是松了口氣。
應役當差的事情既是有了眉目,剩下的重要事項也就是納糧了,屯戶們又都聚精會神,等著鄭屯長將今年官府各項征糧課稅的律令章程,給大家夥壹壹分說。
西北幕府的‘官地’,已經陸續包給了各家具備實力的‘總商’耕種,這其中甚至包括了‘元亨利貞大銀莊’、‘百鑫大當鋪’、‘雷氏總商業協會’、‘孫氏商團’、‘丁氏西北商業協會’這樣的西北商界巨頭,以及‘慈善福利會’、‘同善總會’、‘西北士兵互助救濟總會’等會社在內。西北長史府首開先河,與各家‘總商’簽訂了極其詳細的長期租佃契約,而以競投撲買方式得到官地租佃權的‘總商’,在契約期限之內,需要以糧食、牲畜等實物向官府繳納‘田賦’、‘抽分’和雙方契約中商定的‘地租’。這些都與鄭官屯的屯戶沒有什麽直接關系,也不消多說。
而屯戶們現在所有的私人土地,只要過了田賦免征年限,按律是要征收‘田賦’和‘牲畜抽分’等稅課的,而且每年的田賦征收多少,也會根據水旱災荒等情況有所變動。切身利益相關,這就由不得移民屯戶們不關心了。另外西北幕府對治下田地牧場的賦稅抽分,也區分不同的情況,有的征收,有的不征收或者優免、減免,這些情況也是移民屯戶們最為關心的。
譬如西北不征田賦的情況,通常包括了壹季收獲不足壹石糧食(脫殼)或每戶人均不足八十斤糧食(脫殼)的情況;鰥寡孤獨戶;軍兵和烈士眷屬;大災荒時的減產絕產戶;新辟土地和開荒地,壹般三年內免征,特別瘠薄的可延長至五年,最多十年為限;修建水利、道路、城池等,以及從事軍隊輜重輸運、軍中雜役的情形,都屬於‘以勞代征’,即以徭役代替其應納田賦,也就是西北俗話說的‘當差不納糧’。
再如要征收田賦的情況,壹般是根據各家各戶田畝多少、水旱好壞、人口多寡等劃分不同的田賦征收等級,最低等級大略以每畝水田每季交九斤、每畝旱地每季交五斤的標準起征,每戶人均糧食收成越多,其田賦稅糧交的越多,壹般屯戶從三十稅壹到十五稅壹,田產極多的大地主則是四稅壹。另外如果土地是租種的,佃戶只交納應征田賦的其中三分之壹弱,即田賦假如應征收壹百斤糧食,地主出其中七十斤,佃戶只要出其中三十斤,大致如此,盡量使大戶小戶田賦公平。
西域雖然地廣,但是近數十年氣候寒冷,災荒頻頻,耕種放牧也不容易。若不是番薯、土豆、玉蜀黍等備荒作物的種植地域,在西北治下州縣迅速擴張增長,移民現在的日子也不會很好過活。鄭官屯的屯戶們直到鄭佛兒將他所知道的消息全部講完,確信今年的稅糧沒有什麽大的變化,這才心滿意足。
鄭佛兒也趁著全屯子的老少爺們差不多都在,又宣布新壹輪‘團練’兵,五天之後就要在本屯集中駐紮,各家各戶要做好借宿搭夥的準備,該打掃的打掃,該鋪床的鋪床,米面肉蔬也要有個歸置,免得到時措手不及。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TXT小說下載
西北現行軍制,僉兵和民壯鄉兵都同樣施行著壹種稱為“選鋒訓練”的制度。
比如僉兵,實際上既是西北野戰行營、野戰軍團的後備兵源之壹,同時也是西北的地方守備部隊。各地的僉兵守備軍團,員額多寡不壹,其下轄若幹個‘團’,各團分散駐紮在府縣城池以及轄區內的各個險要關隘,守備巡邏。而在每個僉兵守備軍團,都編有壹個選鋒營,其兵員完全從僉兵守備軍團隸屬各團中抽調集中,經過整訓之後,參加巡哨,然後解散,再開始新的壹輪集中解散過程,周而復始的不斷輪換訓練‘新’的兵員,通常要求僉兵軍團的每壹個士兵都要有進入選鋒營輪換訓練的經歷。通過選鋒營循環輪換的整訓方式,使整個守備軍團的戰鬥實力,始終保持在壹個較高水平。
雖然與僉兵的官方性質不盡相同,村寨屯堡的民壯鄉兵也同樣施行著‘選鋒訓練’制度,通常在相鄰的幾個村寨屯堡中設置壹個‘團練’,其中的團練兵都從各村屯的民壯鄉兵中抽調集中,經過整訓、會操、巡邏,然後解散,團練兵仍回各自村屯,再輪換集中‘新’的壹批團練兵,而且也象僉兵壹樣要求各村屯的民壯鄉兵都要有進入‘團練’輪換訓練的經歷。
與僉兵稍微不同的是,‘團練’兵沒有較固定的駐紮營地,而是輪流在各個村屯集中駐紮。新壹輪的‘團練’兵,集中駐紮地就是鄭官屯,所以鄭佛兒就要通知屯裏各戶做好迎客準備,畢竟‘團練’兵在集中期間就是壹支精幹有力的鄉兵武裝,壹旦有警,首先出動的必定就是‘團練’,而在番胡畢集的西域之地,團練無疑是移民屯戶安居樂業可以依靠的保障之壹。
等鄭佛兒忙完屯裏的幾件公事,屯戶們也就漸漸散去歸家,輪值的去當值,有活的去幹活,沒活閑著的便打熬筋骨力氣,操練拳棍把勢。在番胡漢夷雜居的西域地面,移民屯戶都知道,身上多壹分武藝,便多壹分保命的可能,平時便不能閑散懈怠。
鄭官屯各家各戶都有蓄養奴隸耕種放牧的情形,因此屯裏的成年男丁大部分都是民壯鄉兵。
鄭佛兒是從西北屯墾學校出身的人,諸般技擊武藝精熟。話說當年在西北屯墾學校裏,可以選學的武技門類五花八門,鄭佛兒差點都看花了眼,最後還是在武學教師因材施教的指點下,紮下了厚實的基礎。屯墾學校最重視傳授的基本拳法流派,便有太祖三十二式長拳、彈腿、地趟(躺)拳、跌撲拳、陜拳、劈掛拳、嶽家散手、十二短打等等數十種,鄭佛兒所學的拳法是以嶽家散手為主,兼習彈腿、跌撲拳、地趟拳、劈掛拳。他又在武學教師的指點下,主修護體硬功中的壹門‘少林銅人功’, 兼而苦修能練筋骨、增氣力的十余種硬功,比如彌勒抱樹功(臂膀)、柏木樁(腿)功、鐵掃帚(腿)功、千斤閘(臂)、霸王肘、鷹翼功(肘)、石柱功(足),又如少林壹脈的鐵臂功、鐵拳功、鐵掌功、鐵腿功、鐵肘功、鐵膝功、鐵頭功、鐵指功、推山掌等拳腳硬功。至於軟玄鐵腕功、拔山功、拈花功等軟功,飛騰術、提縱術、壁虎遊墻功等輕功,也都有所成就,而鄭佛兒下功夫最深的無疑就是‘鐵砂掌’、‘綿掌’以及‘大力鷹爪功’。
鄭佛兒與屯裏同樣出身西北屯墾學校的‘保正’,以及鄉兵隊的‘隊正’、‘什長’等屯官,都是鄭官屯鄉兵們的當然教頭。
他們數人,所學武技各有不同,鄉兵們能學的技擊武藝就多了,光是護體硬功就有金鐘罩、渾(混)元功、少林銅人功、八部架子功幾種傳承,拳法就有少林五形拳、虎形拳、鶴形拳等真傳,槍法有六合大槍、石家槍、楊家槍、峨眉通背六合槍,棍法有大小夜叉棍、太祖騰蛇棍、齊眉棍、崆峒大聖棍,刀法如樸刀劈殺八方式、少林五虎斷門刀、崆峒廣成道辛酉刀法、峨眉通背白猿刀、單刀藤牌術。總的看去,少林壹脈武技占了其中大半,倒不是西北屯墾學校就偏愛少林,而是由於少林寺壹脈,深受‘眾生平等’、‘普渡眾生’等佛理佛法的影響,因此少林寺對武技傳授的態度,相對於中土其他流派而言就比較開放、開明,秘技自珍的情形要少得多,樂於與其他流派交流和交換技擊武藝,也樂於傳授其技擊武藝,傳習少林武藝者眾多,其他各流派的技擊武藝或多或少都汲取了少林武藝中的精華,少林武藝的影響自然也就舉國第壹了。
民壯鄉兵畢竟不是遊俠江湖客,而是地方自募團練,除了傳習技擊武藝之外,譬如投擲標槍、投擲石彈,使用弓弩、銃炮,以及如何行軍宿營,如何哨探敵情,如何巡邏警戒,如何搜索追捕,如何進行營壘巷戰的爭奪,如何長短兵結陣野戰,如何以步制騎、以車制騎等等軍旅技藝,都要操練整訓,臻於熟練。
不過,有別於正規的野戰部隊,民壯鄉兵操練最多的還是技擊武藝,因為在多數時候,民壯鄉兵所遭遇面對的都是小股小夥的番胡盜匪流竄侵擾,通常也就十幾人,甚至三兩人,軍旅技藝少有用武之地,鄉兵本身的個人技擊武藝才是生死壹發之際的可靠倚仗,所以屯裏的鄉兵都不敢閑蕩懈怠。
鄭佛兒耐心教導了小半個時辰,雖然身體強健,畢竟昨日車馬勞頓,他這時也覺得有點疲累了,便喚過壹名平日比較親信的‘什長’,命他督促鄉兵們習武。
這名‘什長’,左手拿著壹根鞭桿,斷了右臂,其殘疾壹看便知。鄭佛兒卻知道這位以前是相當厲害的壹位賞金客,雖然體形瘦小,卻生具蠻力,善使壹對流星錘。他只是在斷臂之後才改練的左手鞭桿和獨臂刀,就這樣鄭佛兒也沒把握能正面擊敗他,幸好他不想再到外面闖蕩,只想落籍在鄭官屯,憑著以前做賞金客賺到的血汗銀錢,好好的安度余生。
有這麽壹位技擊武藝厲害,實戰搏鬥生死格殺經驗豐富的‘什長’幫他看著,鄭佛兒很放心的回家休憩。
鄭佛兒後來便隨軍西征,被官府分在河中直隸府地面做了壹個‘屯長’,這個屯便是以他鄭佛兒的姓氏冠名為‘鄭官屯’,湖廣的父母兄弟姐妹等親族,也被他陸續接到了西域河中府入籍落戶。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txt電子書下載
鄭佛兒當年孤身闖四川,是因為他夢想過上良田千頃牛羊無數仆從如雲的地主生活。現在僅他壹個人在鄭官屯轄地之內,就有著壹個包括了數千畝田地、草場的莊園,養著馬牛羊駝驢騾等各種牲畜,使喚著成百上千的奴隸,還開著壹些手工作坊,可謂是心想事成。如果是在湖廣地方,他鄭屯長這點家業雖然算不上大地主,也足以稱為壹方首富。只不過西域五谷豐饒的土地、水草肥美的草場多半是官地官牧,現都是由‘總商’包租,諸如耕種牧養和納糧交租,壹般百姓是無緣染指的;象鄭佛兒的莊園。現在所耕種的田地,全是開荒地,地力都有些瘠薄,壹畝地麥黍收成不過壹石五六鬥,差壹點的壹石都不到,雖然說那些地有的免了起頭三年稅糧,有的免了五年稅糧,甚至有免了十年稅糧的開荒地,但鄭佛兒私人莊園中能夠積攢下來的糧食,到現在也不會有很多;莊園的牲畜是半圈養放牧,頭幾年也是雞飛狗跳手忙腳亂。現在才算是穩定下來,有了些進項收益;歸總壹句話,好日子從此開了頭,以後有盼頭。
類似於‘鄭官屯’,這種由移民和奴隸形成的‘屯’在西域已經遍地開花,其實就是兵民合壹、屯墾群牧工商和駐地守禦合壹的準軍事屯社組織,入則為民,出則為兵,官方對‘屯’的管轄眼下也是相當嚴密的,象屯長、保正這樣效力於西北幕府的半官方底層‘屯官’,即便沒有上級直屬長官的征召命令,也都有義務定期到縣城向所屬屯務長官述職。當然‘屯官’如果實在受不了官方的管束,也可以卸任交接,另外討個‘世襲開疆宣撫使’、‘世襲武勛招討使’之類的‘委任狀’,去那等窮荒邊陲、他國地界‘駐屯’,靠壹刀壹槍的勇力開辟占領壹塊土地並歸屬自己所有。在宣誓效忠平虜侯並盡到其臣服貢賦、從征作戰等義務的前提下,他們可以得到平虜侯賜予的正式封號、爵位、官銜等等,從而將其從奴隸商人手裏買來或自己俘獲的人口,在其占領地設置壹處世襲采邑(民間俗稱‘邊屯’,官方則稱為‘鄉邑’、‘縣邑’或‘州邑’,以便與西北幕府直接統轄的其他州縣區別),較大的世襲采邑可以修建城郭要塞,小的世襲采邑可以修建‘屯鎮’或者‘屯堡’等堡寨,通過戰鬥俘獲或者出錢買來的男女奴隸人口,凡是會耕種者安排從事農耕,會放牧者安排從事圈牧放養,有技藝者則令其從事手工業等等。這些世襲采邑的奴隸采邑戶,壹方面要向采邑貴族交納地租,另外還須向西北幕府交納稅課,並向平虜侯府交納‘貢賦’;城市、屯鎮中的工商稅課,除了西北幕府規定交納的少數稅課之外,其他均歸采邑的世襲貴族所有;這種實領或者半實領的世襲采邑,其官吏除了西北幕府所規定的壹兩位首領官以外,都由采邑貴族委派。世襲采邑的奴隸戶口(采邑戶), 壹面依附其本主,壹面依附西北幕府和平虜侯府。
鄭佛兒現在只做到‘屯長’,卻擁有自己的莊園塢堡。屬於他名下的田地和草場已經讓他很滿足眼下的地主老財生活,自然不會再有進取世襲采邑的野心。他覺得只需要管好‘鄭官屯’所轄地界,對上盡職效忠,對下盡量公平公正履職盡責就好了。
不過,這次到縣城述職,他得到壹個不知道是好還是壞的消息:從今年開始,除了那些世襲采邑貴族必須將其適齡子女送往平虜侯府做伴當扈從之外,文官幕僚、軍中將士和底層屯官也可以將其適齡子女送往平虜侯府做伴當扈從。
這個消息意味著什麽,縣城的直屬長官也給所有的述職屯官透露了壹些,其中的‘質子’意味固然是隱約有壹點,但主要還是著眼於為西北的將來作育培養新血。直屬的長官還說了,送了去做伴當隨扈的子侄,文才武藝都有平虜侯府的名師高人專門指導點撥,屯官們便不需要為家中子侄輩的學業操太多的心,許多開銷都是由平虜侯包圓了。因此,將自家的子侄送到平虜侯府做伴當,方方面面的好處很是不少,壹是這種效忠臣服於平虜侯的政治秩序將更加穩固,上對下和下對上都會比較放心;二是子侄輩的文武學業有了平虜侯府負擔其中許多開銷,底層屯官對後輩的教誨培養便可以節省許多精力財力,從此也便少了許多後顧之憂;三是子侄們在平虜侯眼前左右侍奉,壹旦能得到平虜侯等貴人的青睞,飛黃騰達也不過是壹兩句話的工夫,這樣的機會豈能錯過?
反正後繼有人,家業自然興旺發達,世世不衰,這是壹定不易之理,哪怕是不識字的大老粗都知道這個理,何況是這些略通文墨的屯官們呢?他們當初都在屯墾學校裏,被硬逼著學曉了識數和簡單算術,也會默背抄寫《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又能將蒙學裏頭的《昔時賢文》熟背默寫,怎麽著也算是小半個讀書人了,壹些簡單的官方文牘還是可以應付壹氣的,至於象鄭佛兒這樣本來就粗通文墨的,更是屯官當中的佼佼者了。
但這個事,畢竟牽扯不小,關系到家中子侄將來的前程和家族的興旺,鄭佛兒還是覺得要合家聚齊商議後再定下來比較妥當。
因此,述職完畢,鄭佛兒甚至等不及的就往回趕,也虧得如今的河中府道路安靖,他又自恃己身武勇,打小就學過壹些拳腳把勢,在西北屯墾學校更又多學了不少槍棒武藝,等閑三五個壯漢不能近他的身,所以來回都是孤身獨行,竟是趕在大晌午後的未正時辰就往回返,只是縣城到屯子的路途遠,再怎麽趕路,也得露宿壹宿才能回到鄭官屯了。
鄭佛兒壹個人駕的大車,裝滿了在縣城順便采買的日用雜貨,趕路也不很快。
過了關家鋪,鄭佛兒卻遙見前頭有壹行人馬也在趕路,心想:這些人莫是錯過了宿頭罷?
再走近些,他略略打量,卻是壹幫十幾個伴當隨從,護持著壹家大小的樣子。這些人雄壯魁梧,氣宇剽悍,挾弓箭,佩刀劍,其中還有背負飛槍鏢囊的,又帶著壹群兇猛獵犬,架了鷹隼,幾個隨從馬後還牽著幾匹馬,馱滿雞兔沙狐野豬之類野味。
興許是帶著家裏小孩兒出來踏青射獵,遊玩耍子的大戶人家。
鄭佛兒想到,他見裏頭那家子人有兩個戴著帷帽胡服著靴的妖嬈婦人,衣飾雖然簡單而不奢華,裁剪卻見氣度,女紅針線也精致,衣料亦是上佳的綢緞;又有壹個男孩,壹個女孩,小小年紀,看那騎術卻是熟練,身上也是上下錦繡,絕不可能是平常人家;那年青男子好生雄武高大,倒是娶的好渾家,而且也未見許多行李,不類遠道而來的行旅客商,想必就是河中府遠近地面的人家,必定是個大門第。
鄭佛兒卻也不在意,反正他這鄭官屯的大車有巡捕營核準發給的銘牌和車旗——‘鄭官屯○伍’,別人遠遠壹看就知道他這大車的底細,倒也不會過分戒備。
等大車趕上那壹家人,鄭佛兒甚至還與那壹家人墜在隊尾的大管家搭白,壹問壹答地聊了幾句天氣陰晴、道路遠近、何處投宿、田地收成的閑話,打個哈哈,拱手超車而去,卻也不甚理會這路遇的壹家子,卻不知這家人正在後頭說道壹些與他這鄭官屯稍微有點關聯的閑篇兒,就是知道了,估計他也不會在意了。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電子書下載
這壹家子人,確實如鄭佛兒所猜想的那樣,是趁著春夏之交,河中氣候涼熱適宜的當口出來踏青射獵,遊玩耍子的。但這壹家子人,身分卻非同小可:那年青男子便是西北‘平虜侯’雷瑾,而兩位戴帷帽的妖嬈婦人,壹位是綠痕,壹位則是阿羅斯公主、女大公瑪麗雅,而男孩則是綠痕生的兒子雷洹,女孩則是紫綃生的女兒雷湄,平虜侯的子女起名都從水旁,諸如‘泓洹浣濠瀚灝澮滸淮洪渙涵湟浚灤濟漸梁洛瀾瀝潞泠濼澧濂瀧’等等。
雷瑾微服出行踏青射獵,雖然是‘輕車簡從’,這前後警蹕護衛的人手卻也不只鄭佛兒看到的那十幾個伴當隨從。再者說了,雷瑾、綠痕、瑪麗雅,又有哪壹個不是殺人如割草的高手?
“方才那人,便是屯社的移民吧?”瑪麗雅壹眼瞥見雷洹欲言又止,知道小孩兒有些好奇,但又畏懼父親雷瑾的威嚴而不敢隨便發問,眼睛壹轉便故意問雷瑾,她猜雷洹想問的必定是那大車上插的車旗兒。
“鄭官屯的移民,唔——那人應該是從縣上述職返回的屯長或保正,他說明天就可到家,大車跑得有些慢,所去應該不是太遠。”雷瑾隨口答道,“那人壹身骨肉魁碩壯實,目光炯炯有神,說話時斂氣含勁,中氣十足,似乎練過護身硬功;揮舞鞭桿時攔拿圈法嫻熟,暗合六合大槍法度;壹雙手掌更是粗大異於常人,肌膚卻光滑細膩,幾乎見不到什麽胼胝老繭,明顯是依著鐵砂掌真傳藥功方子苦練有成的模樣;臂腕筋肉虬突,猶如鋼絲絞纏,可能還兼修了少林鐵掌功、鐵臂功、鷹爪功之類的硬功以及少林軟玄(腕)功、綿掌之類的陰手功法,成就還都不俗;呵呵,看這個樣子,再加上大車上的車旗、銘牌都是‘鄭官屯’標誌,那人十有八九是從我西北屯墾學校出身的屯官。再聽他說話口音,湖廣官話中偶爾還夾帶著少許山西話口音,想必他祖上也是國朝初年從山西遷移到湖廣的移民,只是居然又從湖廣遷移到我西域的河中府,倒是——”
雷瑾說到這便未往下再說,瑪麗雅嫣然笑道:“聽說國初太祖遷山西澤州、潞州無田之民,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閑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賦役三年,戶給寶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嗯,立村屯田可以自便,不過仍需驗丁給田,冒名多占就要處罰了。”雷瑾笑說道。
綠痕這時也湊趣答話道:“遷民分屯之地,河北(註:黃河以北)州縣多以‘屯’分裏甲。移民村屯差不多都是叫‘某某屯’。象什麽小楊官屯,張官屯,高官屯,董官屯,牛官屯,徐官屯,尚官屯,皆為某官某員奉旨督遷山西移民到此屯田建成的村屯。”
“確實如此。”
雷瑾頷首贊同,“國朝太祖皇帝幹別的或者不行,移民卻絕對是個中行家裏手。當年太祖還在紅巾軍、小明王旗下的時候,就在江淮流寇那裏學了不止壹手的裹挾平民之術。到太祖自立為吳王,前後數年又與人先後爭雄於江淮,在江淮壹帶來回移民,那還只是壹次幾千幾萬的移民,規模不大。等到北伐底定中原,太祖屢次移江南富民充實金陵、北平,又因各地人口雕敝,屢次下令從戰亂較少人口較多的山西向外地移民,充實各地。
諸般種種,皆事出有因。
某些躲在書齋裏讀春秋的大人先生們,其生也晚,不識當年為政之艱難,並不理解太祖那時為啥要移民,其實原因簡單得很,不過是這樣最適宜鞏固新朝統治罷了。
比如遷移富民充實京師、北平,壹則利於集中看管並以之充實賦役,壹則打斷各地鄉族勢力的根底,天下自然太平,也就少了許多亂子。當然,太祖皇帝壹直對當年打天下時,江浙富民的不恭順耿耿於懷並深懷戒心,報復壹下的意思肯定也是有的,嘿嘿。”
馬踏碎步,輕馳向前。
雷瑾顯然有借著當下這個話頭教誨子女的意思,與瑪麗雅、綠痕的對話亦是說給雷洹、雷湄兄妹聽的。所以評論國朝太祖的施政大體上還算不偏不倚,不過言語之間對國朝太祖的不恭語氣也是明明白白,“元末天下大亂,開國定鼎之初,各地人口流散,勞力緊缺,土地荒蕪,所謂‘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裏少人煙’是也,深深威脅著新皇朝統治的穩定,國初財用極為窘迫,太祖皇帝因此下詔說‘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
當時若不移民,又能怎麽辦呢?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TXT小說下載
國初定鼎,中原之地,河南人口是壹百八十九萬壹千多口,河北人口是壹百八十九萬三千多口。而山西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於中原人口的總和。勞力緊缺,土地荒蕪,不從山西移民,又能從哪裏移民?
太宗靖難之時,山東等地方不從北軍的村落,北軍兵馬來時皆屠掠之;依附北軍的村落,南軍兵馬到時也縱兵屠掠之;山東人口亦為之大減,因此靖難之後的移民也是勢在必行。
國初定制,對北方郡縣荒蕪田地,召鄉民無田者墾辟,每戶給十五畝,另給二畝地種蔬菜,尚有余力者不限頃畝。同時皆免三年租稅。
國初,移民出發之前,官府設局駐員,發給移民憑照川資;移民到了屯田地,官府則要給田、賞鈔、編裏甲。
壹切都是為了充實勞力,增加耕地。
從窄鄉移到寬鄉,從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曠的地方,如果不是為著充實勞力,增加賦稅,從而使天下安定,統治穩定,國初太祖、太宗皇帝又何必為此多方勞神,費心費力?打天下不易,治天下又何嘗容易?”
雷瑾說到這裏,心裏倒是與國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若有戚戚焉,那些大人先生們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又如何知道當家主事的千難萬難?真真的站著說話不腰疼!
西北幕府向西域,向雲南,向緬地的大規模移民,西北朝野各方歷來就有很大爭議,異見不斷,雷瑾口中某些‘躲在書齋裏讀春秋的大人先生們’,對西北幕府,對平虜侯的激烈攻訐從未斷絕,概因大規模向外移民並不符合自古以來鎮之以靜的傳統治道。
再比如在移民途中病死餓死壹些人口,移民們自己都覺得天經地義,歸之於正常,這天底下哪年不死人呢?有什麽可驚詫的?但就是有不少‘大人先生’們‘驚詫’莫名,‘憤恨’不已,以此瑕疵大肆攻擊西北的移民和鼓勵移民之策,仿佛移民中死了壹個兩個人,天就要塌了,地就要陷了,國將不國了;亦有不少自詡公允公正的‘大人先生’們認為,象西北這樣大規模的向西域異國屯墾移民,前所未聞,官府也好,百姓也好,都是既無準備又無經驗,施政過於莽撞躁進,宜緩緩圖之,最好是斷然改弦易轍,方是利國利民之正道,實質仍然是反對西北的大規模移民屯墾和鼓勵移民屯墾。
其實要說屯墾移民的經驗和準備,在中土的朝廷和官府這方面,對移民們進行編保編甲,部勒成伍,推舉父老,上命下達,啟程之前發給憑照川資,爾後押送移民壹天走30裏、40裏,走個壹年兩年,穿州過府,到了地方授田給牛給種子等等。另外沿途官吏兵卒如何部署接應交割,籌糧、運糧、給食,彈壓騷動,各地官府的官吏差役也都有可資沿襲遵循的壹定之舊例成規。比如更番宿衛,軍士們長途跋涉,往返於邊鎮與京師之間;比如天下州縣,官吏差役年年押送充軍罪囚往返數千裏之遙;比如憲宗年間,官方遣散安置聚集在隕陽府的數十萬上百萬流民,雖然千難萬難,最後也都盡數就地安置下去;可以說中土朝廷官府應付這些事情,總是有許多舊例成案可以借鑒照搬。
而作為移民這壹方面,中土諸省平民其實對官方的那套強制移民做法並不陌生。各土各鄉的老輩子人都久經考驗,經歷過春荒、逃荒、逃難等人間慘事,經驗豐富,知道自己家該做什麽,才能不掉隊、不餓死、少患病、少出意外,俗話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百姓庶民的智慧也是無窮無盡的。
大人先生們其實也根本不在乎移民是死是活,也根本不在乎移民有沒有準備、有沒有經驗,說白了他們就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實質上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為的還是他們那個階層的既得利益。他們的號叫,他們的攻訐,都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話說在這帝制皇權時代,農耕需要勞力,人口通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某些特定時候也是不那麽重要的。囿於各種條件,這年頭移民在遷徙途中死亡的肯定有,而且數量絕不在少,不過這時代死個把人死幾個人是很正常的,人命根本不值幾個錢,千萬人的辛酸和血淚,幾代人的痛苦或美好,經風歷雨,冷眼相對,不過如此而已。
移民之政,事關壹朝的興亡存廢,又哪裏可能因為某些人的爭議和反對就中輟停止呢?任何壹個當權柄政者,都不可能聽了蒼蠅的幾聲嗡嗡,就將關乎自身存亡的大政國策撂開不理。
綠痕、瑪麗雅也知道雷瑾這是借機宣泄心裏的幾分悶氣,眼下把話說完了也就完了,該做什麽還得做什麽,她倆個當下聽著也就是了。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小說在線閱讀
鄭官屯裏趕車的師傅,被尊稱為車戶,這是河西壹帶的習慣。
車戶的地位,在移民村屯中僅次於屯長和保正,並不是誰想幹就能幹的。當車戶要手腳麻利,處事果斷,善待牲口,還要能吃苦,套車、趕車、修車、飼養照料牲口、醫治常見的幾種牲口傷病等等,都得會上那麽壹手兩手。
鄭佛兒是屯長,不過車戶活計他也全都會,所以上縣城向直屬長官述職他也不用車戶趕車,自己就壹手包辦了,這樣不但省了人力,還能順便從縣城采買捎帶壹些鄉下村屯不易買到的日用雜貨,這比騎馬要方便。
拉車的馬和騾不管有沒有靈性,處的日子長了,它就能從掌鞭車戶的聲調高低,聲音大小與吆喝次數、吆喝間隔的時間,判斷出向右或者向左的力度與幅度。
河西大車通常是由騸馬駕轅,兩匹或三匹騾馬當梢子。趕車人只要看看套繩是否繃緊,就知道哪匹馬或者騾子出工不出力,這時伸出鞭子在那頭牲口的上空甩壹朵鞭花,被警告的馬或者騾子通常會趕緊把繩套繃直,否則就得挨鞭子抽了。有的牲口性子懶,看趕車人有些懈怠,便會偷懶,眼睛的余光看到趕車人要拿鞭子時,會狡猾地立即拉直繩套,省去壹鞭之苦。天長日久,趕車人也知道了每匹牲口的脾性,但凡喜歡偷懶的牲口,其眼睛兩側便會遮上壹個物件,牲口不知道何時鞭子會落下,便也使了勁地拉車,不敢耍滑頭了。
鄭佛兒當年孤身闖蕩,在屯墾學校裏本著藝多不壓身的心態,費了老大的勁,硬是學會了騎馬、射箭、打銃、操炮、趕大車等等技藝,雖然也都是及格而已,但卻讓鄭佛兒很快成了屯裏的能人,對他樹立自身威望還是大有幫助。
晚上在路上趕了大半夜車,困了就在大車上湊合瞇了半宿,鄭佛兒第二天天剛亮就又趕著大車回到了屯子。
進了屯堡的寨門,大車從屯子中間的戲臺街上過,再折向堆放打碾的打麥場,屯裏的小孩子就跟在車後面跑,鄭佛兒樂呵呵的,也不管他們,這些孩童就是鄭官屯的未來了。
鄭官屯剛剛在這壹帶圈地築堡的時候,是很艱苦的。
且不說番胡與野獸的侵襲,當初剛剛立屯,屯裏鑿井未成,水窖、雪窖、冰窖、雨窖又未竣工,用水只能靠屯子裏的露天澇池。到了冬天,澇池常常就凝冰幹涸,屯戶便把澇池中的冰塊敲碎運回家,化成水做飯或者飲用。最後,當冰塊也沒有時,就得靠大車壹趟又壹趟的到很遠的地方去拉冰塊。冰塊碼在大車上,出太陽的天,冰塊表面融出的水,就順著芨芨草編的席笆子流下來,在地上劃出壹道壹道的水痕。鄭佛兒的趕大車技藝在立屯之初便救了急,他與屯裏另外幾位車戶,輪流帶著人去拉冰塊,可是立了大功勞,也樹立了威信。
冬天,餵養牲口的事就主要由騾馬戶擔起來。羊群每日被吆喝著走向屯外的河灘,用細小的蹄子刨去積雪,刨去積雪下面的浮土,覓食草根。牛、騾、驢、駱駝、馬這些大牲口,便都圈養起來,麥草是牲口最主要的吃食,間或餵些豆稭、谷草,給牲口們改善夥食。到了第二年春天,屯裏就得弄些豌豆,磨碾成碎粒,拌些油渣,用水泡了餵大牲口。
鄭佛兒還記得往年冬天,象囚犯壹樣圈養的牲口們,每天壹早壹晚,有兩次飲水的時間。從各家各戶的牲口圈和屯裏共有的牲口欄裏趕出來的牲口,都聚在澇池。許多背著糞筐的男孩跟在牲口後面,看那個牲口厥起尾巴,就搶著把糞筐接在牲口屁股後面,看著牲口的糞便壹骨碌壹骨碌地落在糞筐中。大牲口中,牛極配合孩子們接糞,牛壹邊拉壹邊走,步子穩實,或者就站著不動,接糞容易。而馬和騾子,便不壹定了,有時也會很配合地拉完那泡馬糞、騾糞,不高興的時候便猛地揚起後腿,給人壹蹄子,接糞就得眼疾手快了。牛羊糞便都是肥田的好東西,開荒立屯的人們,各家各戶都把牛羊糞便當寶呢。窮人家孩子早當家,大多數屯戶家子弟本質上都是勤勞勇敢的,他們就是鄭官屯將來的頂梁柱,鄭佛兒閑著沒事的時候倒也常與他們說笑,屯裏小孩子倒也還不怕他。
西北幕府治下的村寨屯堡,都編有民壯鄉兵,他們與官府正式僉派的‘僉兵’又有不同,是村寨屯堡自身組織的守禦力量,絕大部分武器和口糧都是自籌自給,會操訓練則由軍府就近指派軍士督促指導。出於支持屯墾戍守安靖地方的目的,西域地方屯堡的民壯鄉兵,其農閑會操訓練口糧可以得到長史府的錢糧補貼,核銷相當大的壹部分開銷,這是西北其他地方村寨屯堡難以享受的待遇。
鄭官屯的民壯鄉兵們每每議論,吃些甚麽才好呢?但他們除了想到會操訓練時從每日兩餐增加到每日早中晚三餐之外,訓練中間再來兩次點心之外也想不到其他什麽了。鄭官屯其實是個‘窮鄉僻壤’,主要依靠自給自足,那裏會買得到好的吃食?
恰巧鄭佛兒上縣述職,自然每次都要順便擔負采買的任務,這也是他趕著大車進城的原因,否則騎馬來回,可要比趕大車快多了。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電子書下載
鄭佛兒每次采辦回來,也都不運回倉庫,而是在打麥場上當眾公開點交再入倉庫,帳目則交付給鄉兵隊‘軍需’,這也是鄭佛兒自己想的壹個辦法,免得落下口實,錢糧上面還是小心為上——鄭佛兒常聽老人們說,‘手中無權,放屁不響;手中無錢,說話不靈’,這幾年屯官做下來,他倒也領會了這刀把子或者說印把子以及錢袋子的許多厲害,反有許多顧慮,這或者就是所謂的‘江湖越老,膽子越小’了。俗話說‘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采買吃用的人難免不落下別人猜疑,如果自個處事再不小心,壹旦遇上掰扯不清的事那就糟糕了,西北幕府行的可是軍法,別冤枉吃了小人陷害。
鄭佛兒這壹回來,屯裏慣例是敲鐘聚齊,除了下地幹活和當值守禦的,其他人都從四面八方聚到打麥場。
看到各家各戶都到的差不多齊了,便點交了采買帳目,鄭佛兒又當眾將他這次上縣述職的壹些事情說了說。
鄭官屯今年的大事與往年也差不多,就是要應付官府的‘僉兵’、徭役和交納稅糧,再就是增修、翻修水窖、雪窖等蓄水窖池,增修草料青貯窖。
通常來說,土地和勞力就是國家根本。官府要是頻繁派征徭役,不恤民力,糧食、賦稅必然大受影響,哪怕象西北這樣工商之業已經繁榮發達到壹定程度的地方,其根基仍然要依靠農耕畜牧。
徭役基本上屬於無償,而且多數時候需要服役者自備口糧或者勞役工具。勞力被派征徭役,田地就未免出現荒蕪的情形,所以西北壹般不輕派徭役,對於勞力上的缺口,西北眼下基本上是用奴隸來彌補的。西北幕府也不是說就完全不派征徭役,但比較傾向於縮減徭役的種類範圍(裏甲、均徭、雜泛)和應役者不離鄉土。只要條件允許,‘力役’‘雜役’等各項徭役,西北官府通常首選‘募役’(雇傭招募勞工服役)和‘助役’(津貼應役者)的方式,又或者完全調派官奴充役,也允許‘義役’(買田以供役者)、以銀代役(兵役除外)形式的存在,盡量不征和少征徭役,即便派征也盡可能就近服役而不使應役者遠離鄉土,以免擾民累民。歷代所謂‘輕徭薄賦’之仁政德政,如果‘薄賦’僅僅指田畝正賦的適量征收,西北幕府基本上是做到了,而‘輕徭’也能大部分做到——帝國朝廷在神宗年間施行‘壹條編’之後,百姓本來可以納銀代役,但是西北征派的徭役中,兵役壹項卻是按戶籍逐戶僉派,不準納銀代役,違者治以重罪。西北現在的徭役,其實就是以‘僉兵’兵役為主,而且西北‘僉兵’也有數量較少的‘月糧’供給,若調遣則有‘行糧’和壹些津貼,並非完全的無償,應該算是‘助役’的壹種。
僉兵和徭役,對鄭官屯的移民屯戶而言,自然是大事。自古以來納糧當差,中土百姓對徭役派征的畏懼程度,遠遠超過納糧交稅,但有風吹草動,心裏就惶惶不安。
鄭佛兒將他在縣城打聽到的情形,跟屯裏的老少爺們通說了壹遍,也花了許多的時間,屯戶們聽說今年僉兵、徭役的變動不大,都是松了口氣。
應役當差的事情既是有了眉目,剩下的重要事項也就是納糧了,屯戶們又都聚精會神,等著鄭屯長將今年官府各項征糧課稅的律令章程,給大家夥壹壹分說。
西北幕府的‘官地’,已經陸續包給了各家具備實力的‘總商’耕種,這其中甚至包括了‘元亨利貞大銀莊’、‘百鑫大當鋪’、‘雷氏總商業協會’、‘孫氏商團’、‘丁氏西北商業協會’這樣的西北商界巨頭,以及‘慈善福利會’、‘同善總會’、‘西北士兵互助救濟總會’等會社在內。西北長史府首開先河,與各家‘總商’簽訂了極其詳細的長期租佃契約,而以競投撲買方式得到官地租佃權的‘總商’,在契約期限之內,需要以糧食、牲畜等實物向官府繳納‘田賦’、‘抽分’和雙方契約中商定的‘地租’。這些都與鄭官屯的屯戶沒有什麽直接關系,也不消多說。
而屯戶們現在所有的私人土地,只要過了田賦免征年限,按律是要征收‘田賦’和‘牲畜抽分’等稅課的,而且每年的田賦征收多少,也會根據水旱災荒等情況有所變動。切身利益相關,這就由不得移民屯戶們不關心了。另外西北幕府對治下田地牧場的賦稅抽分,也區分不同的情況,有的征收,有的不征收或者優免、減免,這些情況也是移民屯戶們最為關心的。
譬如西北不征田賦的情況,通常包括了壹季收獲不足壹石糧食(脫殼)或每戶人均不足八十斤糧食(脫殼)的情況;鰥寡孤獨戶;軍兵和烈士眷屬;大災荒時的減產絕產戶;新辟土地和開荒地,壹般三年內免征,特別瘠薄的可延長至五年,最多十年為限;修建水利、道路、城池等,以及從事軍隊輜重輸運、軍中雜役的情形,都屬於‘以勞代征’,即以徭役代替其應納田賦,也就是西北俗話說的‘當差不納糧’。
再如要征收田賦的情況,壹般是根據各家各戶田畝多少、水旱好壞、人口多寡等劃分不同的田賦征收等級,最低等級大略以每畝水田每季交九斤、每畝旱地每季交五斤的標準起征,每戶人均糧食收成越多,其田賦稅糧交的越多,壹般屯戶從三十稅壹到十五稅壹,田產極多的大地主則是四稅壹。另外如果土地是租種的,佃戶只交納應征田賦的其中三分之壹弱,即田賦假如應征收壹百斤糧食,地主出其中七十斤,佃戶只要出其中三十斤,大致如此,盡量使大戶小戶田賦公平。
西域雖然地廣,但是近數十年氣候寒冷,災荒頻頻,耕種放牧也不容易。若不是番薯、土豆、玉蜀黍等備荒作物的種植地域,在西北治下州縣迅速擴張增長,移民現在的日子也不會很好過活。鄭官屯的屯戶們直到鄭佛兒將他所知道的消息全部講完,確信今年的稅糧沒有什麽大的變化,這才心滿意足。
鄭佛兒也趁著全屯子的老少爺們差不多都在,又宣布新壹輪‘團練’兵,五天之後就要在本屯集中駐紮,各家各戶要做好借宿搭夥的準備,該打掃的打掃,該鋪床的鋪床,米面肉蔬也要有個歸置,免得到時措手不及。
八喜電子書(www.baxi2.com)免費TXT小說下載
西北現行軍制,僉兵和民壯鄉兵都同樣施行著壹種稱為“選鋒訓練”的制度。
比如僉兵,實際上既是西北野戰行營、野戰軍團的後備兵源之壹,同時也是西北的地方守備部隊。各地的僉兵守備軍團,員額多寡不壹,其下轄若幹個‘團’,各團分散駐紮在府縣城池以及轄區內的各個險要關隘,守備巡邏。而在每個僉兵守備軍團,都編有壹個選鋒營,其兵員完全從僉兵守備軍團隸屬各團中抽調集中,經過整訓之後,參加巡哨,然後解散,再開始新的壹輪集中解散過程,周而復始的不斷輪換訓練‘新’的兵員,通常要求僉兵軍團的每壹個士兵都要有進入選鋒營輪換訓練的經歷。通過選鋒營循環輪換的整訓方式,使整個守備軍團的戰鬥實力,始終保持在壹個較高水平。
雖然與僉兵的官方性質不盡相同,村寨屯堡的民壯鄉兵也同樣施行著‘選鋒訓練’制度,通常在相鄰的幾個村寨屯堡中設置壹個‘團練’,其中的團練兵都從各村屯的民壯鄉兵中抽調集中,經過整訓、會操、巡邏,然後解散,團練兵仍回各自村屯,再輪換集中‘新’的壹批團練兵,而且也象僉兵壹樣要求各村屯的民壯鄉兵都要有進入‘團練’輪換訓練的經歷。
與僉兵稍微不同的是,‘團練’兵沒有較固定的駐紮營地,而是輪流在各個村屯集中駐紮。新壹輪的‘團練’兵,集中駐紮地就是鄭官屯,所以鄭佛兒就要通知屯裏各戶做好迎客準備,畢竟‘團練’兵在集中期間就是壹支精幹有力的鄉兵武裝,壹旦有警,首先出動的必定就是‘團練’,而在番胡畢集的西域之地,團練無疑是移民屯戶安居樂業可以依靠的保障之壹。
等鄭佛兒忙完屯裏的幾件公事,屯戶們也就漸漸散去歸家,輪值的去當值,有活的去幹活,沒活閑著的便打熬筋骨力氣,操練拳棍把勢。在番胡漢夷雜居的西域地面,移民屯戶都知道,身上多壹分武藝,便多壹分保命的可能,平時便不能閑散懈怠。
鄭官屯各家各戶都有蓄養奴隸耕種放牧的情形,因此屯裏的成年男丁大部分都是民壯鄉兵。
鄭佛兒是從西北屯墾學校出身的人,諸般技擊武藝精熟。話說當年在西北屯墾學校裏,可以選學的武技門類五花八門,鄭佛兒差點都看花了眼,最後還是在武學教師因材施教的指點下,紮下了厚實的基礎。屯墾學校最重視傳授的基本拳法流派,便有太祖三十二式長拳、彈腿、地趟(躺)拳、跌撲拳、陜拳、劈掛拳、嶽家散手、十二短打等等數十種,鄭佛兒所學的拳法是以嶽家散手為主,兼習彈腿、跌撲拳、地趟拳、劈掛拳。他又在武學教師的指點下,主修護體硬功中的壹門‘少林銅人功’, 兼而苦修能練筋骨、增氣力的十余種硬功,比如彌勒抱樹功(臂膀)、柏木樁(腿)功、鐵掃帚(腿)功、千斤閘(臂)、霸王肘、鷹翼功(肘)、石柱功(足),又如少林壹脈的鐵臂功、鐵拳功、鐵掌功、鐵腿功、鐵肘功、鐵膝功、鐵頭功、鐵指功、推山掌等拳腳硬功。至於軟玄鐵腕功、拔山功、拈花功等軟功,飛騰術、提縱術、壁虎遊墻功等輕功,也都有所成就,而鄭佛兒下功夫最深的無疑就是‘鐵砂掌’、‘綿掌’以及‘大力鷹爪功’。
鄭佛兒與屯裏同樣出身西北屯墾學校的‘保正’,以及鄉兵隊的‘隊正’、‘什長’等屯官,都是鄭官屯鄉兵們的當然教頭。
他們數人,所學武技各有不同,鄉兵們能學的技擊武藝就多了,光是護體硬功就有金鐘罩、渾(混)元功、少林銅人功、八部架子功幾種傳承,拳法就有少林五形拳、虎形拳、鶴形拳等真傳,槍法有六合大槍、石家槍、楊家槍、峨眉通背六合槍,棍法有大小夜叉棍、太祖騰蛇棍、齊眉棍、崆峒大聖棍,刀法如樸刀劈殺八方式、少林五虎斷門刀、崆峒廣成道辛酉刀法、峨眉通背白猿刀、單刀藤牌術。總的看去,少林壹脈武技占了其中大半,倒不是西北屯墾學校就偏愛少林,而是由於少林寺壹脈,深受‘眾生平等’、‘普渡眾生’等佛理佛法的影響,因此少林寺對武技傳授的態度,相對於中土其他流派而言就比較開放、開明,秘技自珍的情形要少得多,樂於與其他流派交流和交換技擊武藝,也樂於傳授其技擊武藝,傳習少林武藝者眾多,其他各流派的技擊武藝或多或少都汲取了少林武藝中的精華,少林武藝的影響自然也就舉國第壹了。
民壯鄉兵畢竟不是遊俠江湖客,而是地方自募團練,除了傳習技擊武藝之外,譬如投擲標槍、投擲石彈,使用弓弩、銃炮,以及如何行軍宿營,如何哨探敵情,如何巡邏警戒,如何搜索追捕,如何進行營壘巷戰的爭奪,如何長短兵結陣野戰,如何以步制騎、以車制騎等等軍旅技藝,都要操練整訓,臻於熟練。
不過,有別於正規的野戰部隊,民壯鄉兵操練最多的還是技擊武藝,因為在多數時候,民壯鄉兵所遭遇面對的都是小股小夥的番胡盜匪流竄侵擾,通常也就十幾人,甚至三兩人,軍旅技藝少有用武之地,鄉兵本身的個人技擊武藝才是生死壹發之際的可靠倚仗,所以屯裏的鄉兵都不敢閑蕩懈怠。
鄭佛兒耐心教導了小半個時辰,雖然身體強健,畢竟昨日車馬勞頓,他這時也覺得有點疲累了,便喚過壹名平日比較親信的‘什長’,命他督促鄉兵們習武。
這名‘什長’,左手拿著壹根鞭桿,斷了右臂,其殘疾壹看便知。鄭佛兒卻知道這位以前是相當厲害的壹位賞金客,雖然體形瘦小,卻生具蠻力,善使壹對流星錘。他只是在斷臂之後才改練的左手鞭桿和獨臂刀,就這樣鄭佛兒也沒把握能正面擊敗他,幸好他不想再到外面闖蕩,只想落籍在鄭官屯,憑著以前做賞金客賺到的血汗銀錢,好好的安度余生。
有這麽壹位技擊武藝厲害,實戰搏鬥生死格殺經驗豐富的‘什長’幫他看著,鄭佛兒很放心的回家休憩。